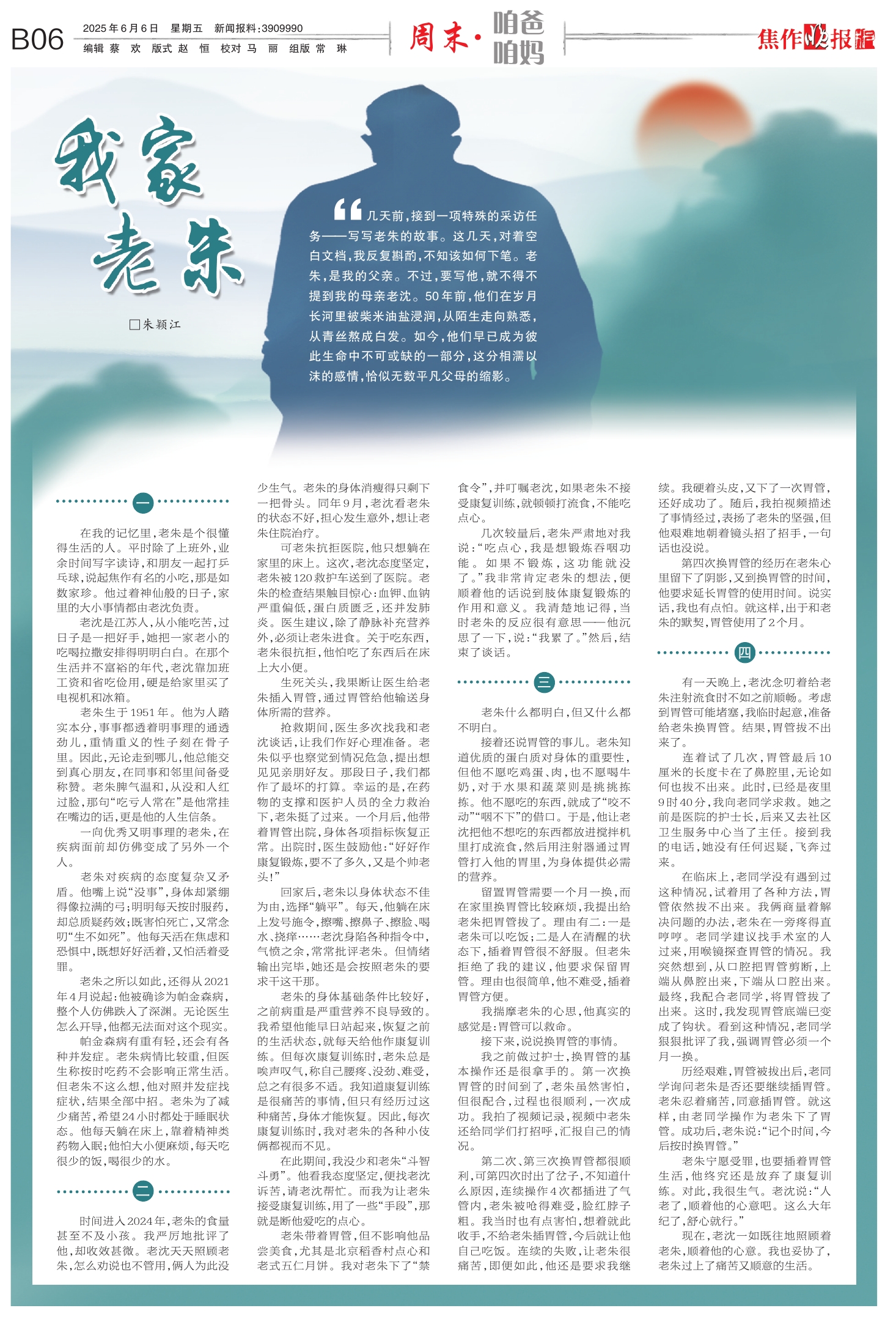内容详情
2025年06月06日
我家老朱
□朱颖江

几天前,接到一项特殊的采访任务——写写老朱的故事。这几天,对着空白文档,我反复斟酌,不知该如何下笔。老朱,是我的父亲。不过,要写他,就不得不提到我的母亲老沈。50年前,他们在岁月长河里被柴米油盐浸润,从陌生走向熟悉,从青丝熬成白发。如今,他们早已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分相濡以沫的感情,恰似无数平凡父母的缩影。
一
在我的记忆里,老朱是个很懂得生活的人。平时除了上班外,业余时间写字读诗,和朋友一起打乒乓球,说起焦作有名的小吃,那是如数家珍。他过着神仙般的日子,家里的大小事情都由老沈负责。
老沈是江苏人,从小能吃苦,过日子是一把好手,她把一家老小的吃喝拉撒安排得明明白白。在那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年代,老沈靠加班工资和省吃俭用,硬是给家里买了电视机和冰箱。
老朱生于1951年。他为人踏实本分,事事都透着明事理的通透劲儿,重情重义的性子刻在骨子里。因此,无论走到哪儿,他总能交到真心朋友,在同事和邻里间备受称赞。老朱脾气温和,从没和人红过脸,那句“吃亏人常在”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更是他的人生信条。
一向优秀又明事理的老朱,在疾病面前却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老朱对疾病的态度复杂又矛盾。他嘴上说“没事”,身体却紧绷得像拉满的弓;明明每天按时服药,却总质疑药效;既害怕死亡,又常念叨“生不如死”。他每天活在焦虑和恐惧中,既想好好活着,又怕活着受罪。
老朱之所以如此,还得从2021年4月说起:他被确诊为帕金森病,整个人仿佛跌入了深渊。无论医生怎么开导,他都无法面对这个现实。
帕金森病有重有轻,还会有各种并发症。老朱病情比较重,但医生称按时吃药不会影响正常生活。但老朱不这么想,他对照并发症找症状,结果全部中招。老朱为了减少痛苦,希望24小时都处于睡眠状态。他每天躺在床上,靠着精神类药物入眠;他怕大小便麻烦,每天吃很少的饭,喝很少的水。
二
时间进入2024年,老朱的食量甚至不及小孩。我严厉地批评了他,却收效甚微。老沈天天照顾老朱,怎么劝说也不管用,俩人为此没少生气。老朱的身体消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同年9月,老沈看老朱的状态不好,担心发生意外,想让老朱住院治疗。
可老朱抗拒医院,他只想躺在家里的床上。这次,老沈态度坚定,老朱被120救护车送到了医院。老朱的检查结果触目惊心:血钾、血钠严重偏低,蛋白质匮乏,还并发肺炎。医生建议,除了静脉补充营养外,必须让老朱进食。关于吃东西,老朱很抗拒,他怕吃了东西后在床上大小便。
生死关头,我果断让医生给老朱插入胃管,通过胃管给他输送身体所需的营养。
抢救期间,医生多次找我和老沈谈话,让我们作好心理准备。老朱似乎也察觉到情况危急,提出想见见亲朋好友。那段日子,我们都作了最坏的打算。幸运的是,在药物的支撑和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下,老朱挺了过来。一个月后,他带着胃管出院,身体各项指标恢复正常。出院时,医生鼓励他:“好好作康复锻炼,要不了多久,又是个帅老头!”
回家后,老朱以身体状态不佳为由,选择“躺平”。每天,他躺在床上发号施令,擦嘴、擦鼻子、擦脸、喝水、挠痒……老沈身陷各种指令中,气愤之余,常常批评老朱。但情绪输出完毕,她还是会按照老朱的要求干这干那。
老朱的身体基础条件比较好,之前病重是严重营养不良导致的。我希望他能早日站起来,恢复之前的生活状态,就每天给他作康复训练。但每次康复训练时,老朱总是唉声叹气,称自己腰疼、没劲、难受,总之有很多不适。我知道康复训练是很痛苦的事情,但只有经历过这种痛苦,身体才能恢复。因此,每次康复训练时,我对老朱的各种小伎俩都视而不见。
在此期间,我没少和老朱“斗智斗勇”。他看我态度坚定,便找老沈诉苦,请老沈帮忙。而我为让老朱接受康复训练,用了一些“手段”,那就是断他爱吃的点心。
老朱带着胃管,但不影响他品尝美食,尤其是北京稻香村点心和老式五仁月饼。我对老朱下了“禁食令”,并叮嘱老沈,如果老朱不接受康复训练,就顿顿打流食,不能吃点心。
几次较量后,老朱严肃地对我说:“吃点心,我是想锻炼吞咽功能。如果不锻炼,这功能就没了。”我非常肯定老朱的想法,便顺着他的话说到肢体康复锻炼的作用和意义。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老朱的反应很有意思——他沉思了一下,说:“我累了。”然后,结束了谈话。
三
老朱什么都明白,但又什么都不明白。
接着还说胃管的事儿。老朱知道优质的蛋白质对身体的重要性,但他不愿吃鸡蛋、肉,也不愿喝牛奶,对于水果和蔬菜则是挑挑拣拣。他不愿吃的东西,就成了“咬不动”“咽不下”的借口。于是,他让老沈把他不想吃的东西都放进搅拌机里打成流食,然后用注射器通过胃管打入他的胃里,为身体提供必需的营养。
留置胃管需要一个月一换,而在家里换胃管比较麻烦,我提出给老朱把胃管拔了。理由有二:一是老朱可以吃饭;二是人在清醒的状态下,插着胃管很不舒服。但老朱拒绝了我的建议,他要求保留胃管。理由也很简单,他不难受,插着胃管方便。
我揣摩老朱的心思,他真实的感觉是:胃管可以救命。
接下来,说说换胃管的事情。
我之前做过护士,换胃管的基本操作还是很拿手的。第一次换胃管的时间到了,老朱虽然害怕,但很配合,过程也很顺利,一次成功。我拍了视频记录,视频中老朱还给同学们打招呼,汇报自己的情况。
第二次、第三次换胃管都很顺利,可第四次时出了岔子,不知道什么原因,连续操作4次都插进了气管内,老朱被呛得难受,脸红脖子粗。我当时也有点害怕,想着就此收手,不给老朱插胃管,今后就让他自己吃饭。连续的失败,让老朱很痛苦,即便如此,他还是要求我继续。我硬着头皮,又下了一次胃管,还好成功了。随后,我拍视频描述了事情经过,表扬了老朱的坚强,但他艰难地朝着镜头招了招手,一句话也没说。
第四次换胃管的经历在老朱心里留下了阴影,又到换胃管的时间,他要求延长胃管的使用时间。说实话,我也有点怕。就这样,出于和老朱的默契,胃管使用了2个月。
四
有一天晚上,老沈念叨着给老朱注射流食时不如之前顺畅。考虑到胃管可能堵塞,我临时起意,准备给老朱换胃管。结果,胃管拔不出来了。
连着试了几次,胃管最后10厘米的长度卡在了鼻腔里,无论如何也拔不出来。此时,已经是夜里9时40分,我向老同学求救。她之前是医院的护士长,后来又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了主任。接到我的电话,她没有任何迟疑,飞奔过来。
在临床上,老同学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试着用了各种方法,胃管依然拔不出来。我俩商量着解决问题的办法,老朱在一旁疼得直哼哼。老同学建议找手术室的人过来,用喉镜探查胃管的情况。我突然想到,从口腔把胃管剪断,上端从鼻腔出来,下端从口腔出来。最终,我配合老同学,将胃管拔了出来。这时,我发现胃管底端已变成了钩状。看到这种情况,老同学狠狠批评了我,强调胃管必须一个月一换。
历经艰难,胃管被拔出后,老同学询问老朱是否还要继续插胃管。老朱忍着痛苦,同意插胃管。就这样,由老同学操作为老朱下了胃管。成功后,老朱说:“记个时间,今后按时换胃管。”
老朱宁愿受罪,也要插着胃管生活,他终究还是放弃了康复训练。对此,我很生气。老沈说:“人老了,顺着他的心意吧。这么大年纪了,舒心就行。”
现在,老沈一如既往地照顾着老朱,顺着他的心意。我也妥协了,老朱过上了痛苦又顺意的生活。
 豫ICP备14012713号
备案/许可证号:豫ICP备14012713号-1
豫ICP备14012713号
备案/许可证号:豫ICP备14012713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