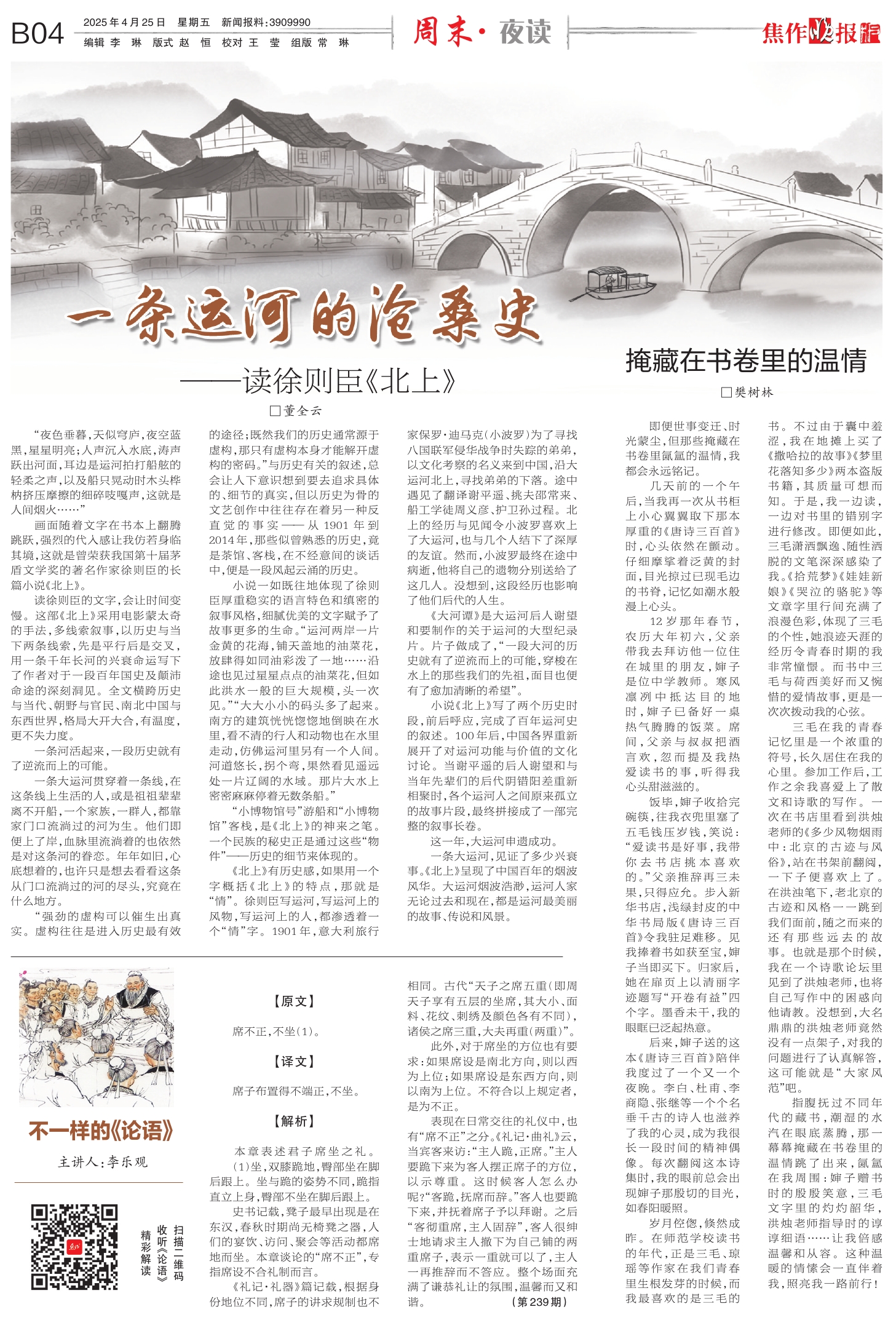内容详情
2025年04月25日
一条运河的沧桑史
——读徐则臣《北上》

□董全云
“夜色垂暮,天似穹庐,夜空蓝黑,星星明亮;人声沉入水底,涛声跃出河面,耳边是运河拍打船舷的轻柔之声,以及船只晃动时木头桦枘挤压摩擦的细碎吱嘎声,这就是人间烟火……”
画面随着文字在书本上翻腾跳跃,强烈的代入感让我仿若身临其境,这就是曾荣获我国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
读徐则臣的文字,会让时间变慢。这部《北上》采用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多线索叙事,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先是平行后是交叉,用一条千年长河的兴衰命运写下了作者对于一段百年国史及颠沛命途的深刻洞见。全文横跨历史与当代、朝野与官民、南北中国与东西世界,格局大开大合,有温度,更不失力度。
一条河活起来,一段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
一条大运河贯穿着一条线,在这条线上生活的人,或是祖祖辈辈离不开船,一个家族,一群人,都靠家门口流淌过的河为生。他们即便上了岸,血脉里流淌着的也依然是对这条河的眷恋。年年如旧,心底想着的,也许只是想去看看这条从门口流淌过的河的尽头,究竟在什么地方。
“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虚构往往是进入历史最有效的途径;既然我们的历史通常源于虚构,那只有虚构本身才能解开虚构的密码。”与历史有关的叙述,总会让人下意识想到要去追求具体的、细节的真实,但以历史为骨的文艺创作中往往存在着另一种反直觉的事实——从1901年到2014年,那些似曾熟悉的历史,竟是茶馆、客栈,在不经意间的谈话中,便是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
小说一如既往地体现了徐则臣厚重稳实的语言特色和缜密的叙事风格,细腻优美的文字赋予了故事更多的生命。“运河两岸一片金黄的花海,铺天盖地的油菜花,放肆得如同油彩泼了一地……沿途也见过星星点点的油菜花,但如此洪水一般的巨大规模,头一次见。”“大大小小的码头多了起来。南方的建筑恍恍惚惚地倒映在水里,看不清的行人和动物也在水里走动,仿佛运河里另有一个人间。河道悠长,拐个弯,果然看见遥远处一片辽阔的水域。那片大水上密密麻麻停着无数条船。”
“小博物馆号”游船和“小博物馆”客栈,是《北上》的神来之笔。一个民族的秘史正是通过这些“物件”——历史的细节来体现的。
《北上》有历史感,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北上》的特点,那就是“情”。徐则臣写运河,写运河上的风物,写运河上的人,都渗透着一个“情”字。1901年,意大利旅行家保罗·迪马克(小波罗)为了寻找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失踪的弟弟,以文化考察的名义来到中国,沿大运河北上,寻找弟弟的下落。途中遇见了翻译谢平遥、挑夫邵常来、船工学徒周义彦、护卫孙过程。北上的经历与见闻令小波罗喜欢上了大运河,也与几个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小波罗最终在途中病逝,他将自己的遗物分别送给了这几人。没想到,这段经历也影响了他们后代的人生。
《大河谭》是大运河后人谢望和要制作的关于运河的大型纪录片。片子做成了,“一段大河的历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穿梭在水上的那些我们的先祖,面目也便有了愈加清晰的希望”。
小说《北上》写了两个历史时段,前后呼应,完成了百年运河史的叙述。100年后,中国各界重新展开了对运河功能与价值的文化讨论。当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阴错阳差重新相聚时,各个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长卷。
这一年,大运河申遗成功。
一条大运河,见证了多少兴衰事。《北上》呈现了中国百年的烟波风华。大运河烟波浩渺,运河人家无论过去和现在,都是运河最美丽的故事、传说和风景。
 豫ICP备14012713号
备案/许可证号:豫ICP备14012713号-1
豫ICP备14012713号
备案/许可证号:豫ICP备14012713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