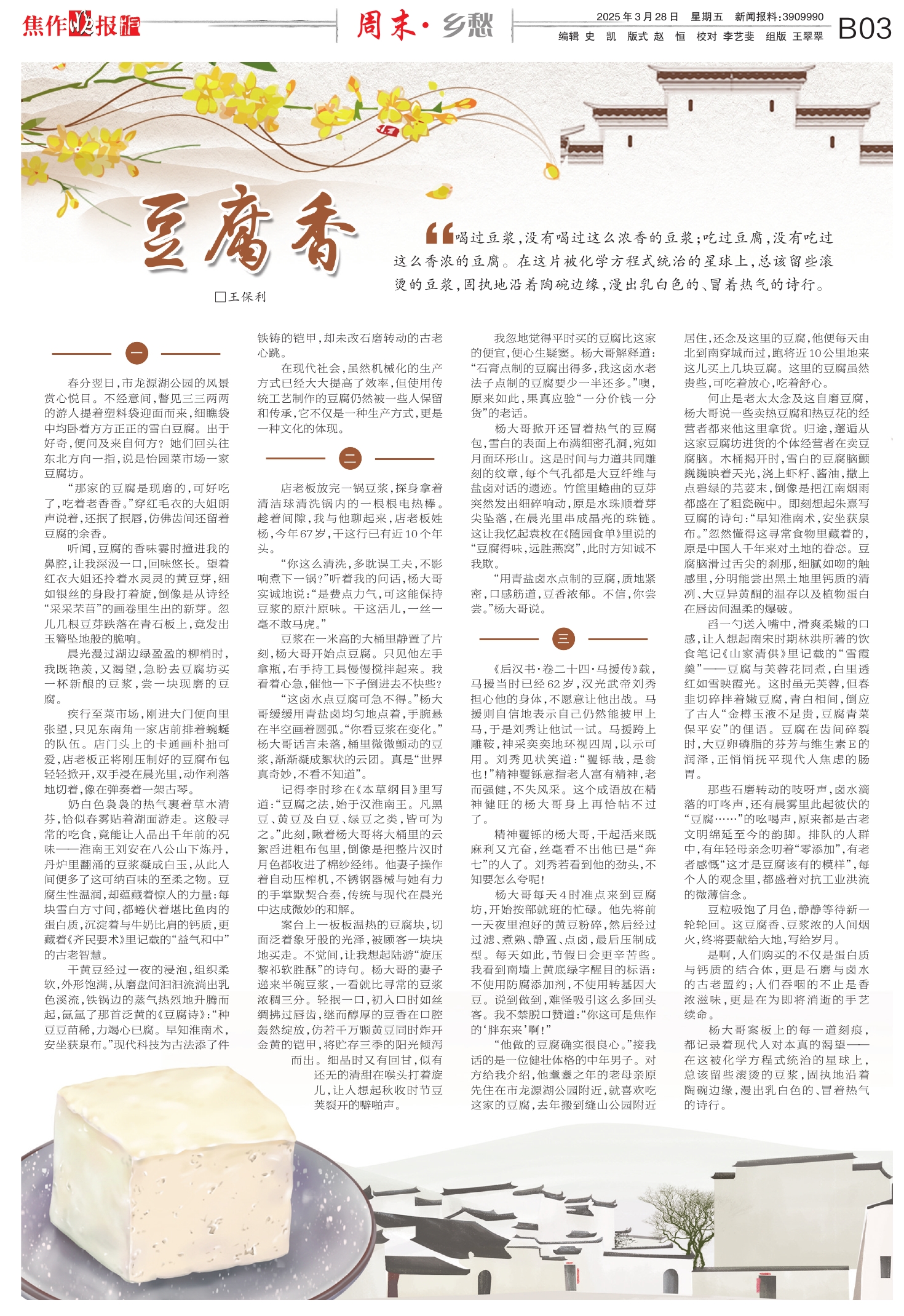еҶ…е®№иҜҰжғ…
2025е№ҙ03жңҲ28ж—Ҙ
иұҶи…җйҰҷ
в–ЎзҺӢдҝқеҲ©
е–қиҝҮиұҶжөҶпјҢжІЎжңүе–қиҝҮиҝҷд№Ҳжө“йҰҷзҡ„иұҶжөҶпјӣеҗғиҝҮиұҶи…җпјҢжІЎжңүеҗғиҝҮиҝҷд№ҲйҰҷжө“зҡ„иұҶи…җгҖӮеңЁиҝҷзүҮиў«еҢ–еӯҰж–№зЁӢејҸз»ҹжІ»зҡ„жҳҹзҗғдёҠпјҢжҖ»иҜҘз•ҷдәӣж»ҡзғ«зҡ„иұҶжөҶпјҢеӣәжү§ең°жІҝзқҖйҷ¶зў—иҫ№зјҳпјҢжј«еҮәд№ізҷҪиүІзҡ„гҖҒеҶ’зқҖзғӯж°”зҡ„иҜ—иЎҢгҖӮ
дёҖ
жҳҘеҲҶзҝҢж—ҘпјҢеёӮйҫҷжәҗж№–е…¬еӣӯзҡ„йЈҺжҷҜиөҸеҝғжӮҰзӣ®гҖӮдёҚз»Ҹж„Ҹй—ҙпјҢзһҘи§ҒдёүдёүдёӨдёӨзҡ„жёёдәәжҸҗзқҖеЎ‘ж–ҷиўӢиҝҺйқўиҖҢжқҘпјҢз»Ҷзһ§иўӢдёӯеқҮеҚ§зқҖж–№ж–№жӯЈжӯЈзҡ„йӣӘзҷҪиұҶи…җгҖӮеҮәдәҺеҘҪеҘҮпјҢдҫҝй—®еҸҠжқҘиҮӘдҪ•ж–№пјҹеҘ№д»¬еӣһеӨҙеҫҖдёңеҢ—ж–№еҗ‘дёҖжҢҮпјҢиҜҙжҳҜжҖЎеӣӯиҸңеёӮеңәдёҖ家иұҶи…җеқҠгҖӮ
“йӮЈе®¶зҡ„иұҶи…җжҳҜзҺ°зЈЁзҡ„пјҢеҸҜеҘҪеҗғдәҶпјҢеҗғзқҖиҖҒйҰҷйҰҷгҖӮ”з©ҝзәўжҜӣиЎЈзҡ„еӨ§е§җжң—еЈ°иҜҙзқҖпјҢиҝҳжҠҝдәҶжҠҝе”ҮпјҢд»ҝдҪӣйҪҝй—ҙиҝҳз•ҷзқҖиұҶи…җзҡ„дҪҷйҰҷгҖӮ
еҗ¬й—»пјҢиұҶи…җзҡ„йҰҷе‘ійңҺж—¶ж’һиҝӣжҲ‘зҡ„йј»и…”пјҢи®©жҲ‘ж·ұжұІдёҖеҸЈпјҢеӣһе‘іжӮ й•ҝгҖӮжңӣзқҖзәўиЎЈеӨ§е§җиҝҳжӢҺзқҖж°ҙзҒөзҒөзҡ„й»„иұҶиҠҪпјҢз»ҶеҰӮ银дёқзҡ„иә«ж®өжү“зқҖж—ӢпјҢеҖ’еғҸжҳҜд»ҺиҜ—з»Ҹ“йҮҮйҮҮиҠЈиӢў”зҡ„з”»еҚ·йҮҢз”ҹеҮәзҡ„ж–°иҠҪгҖӮеҝҪе„ҝеҮ ж №иұҶиҠҪи·ҢиҗҪеңЁйқ’зҹіжқҝдёҠпјҢз«ҹеҸ‘еҮәзҺүз°Әеқ ең°иҲ¬зҡ„и„Ҷе“ҚгҖӮ
жҷЁе…үжј«иҝҮж№–иҫ№з»ҝзӣҲзӣҲзҡ„жҹіжўўж—¶пјҢжҲ‘ж—ўиүізҫЎпјҢеҸҲжёҙжңӣпјҢжҖҘзӣјеҺ»иұҶи…җеқҠд№°дёҖжқҜж–°й…ҝзҡ„иұҶжөҶпјҢе°қдёҖеқ—зҺ°зЈЁзҡ„иұҶи…җгҖӮ
з–ҫиЎҢиҮіиҸңеёӮеңәпјҢеҲҡиҝӣеӨ§й—Ёдҫҝеҗ‘йҮҢеј жңӣпјҢеҸӘи§ҒдёңеҚ—и§’дёҖ家еә—еүҚжҺ’зқҖиңҝиң’зҡ„йҳҹдјҚгҖӮеә—й—ЁеӨҙдёҠзҡ„еҚЎйҖҡз”»жңҙжӢҷеҸҜзҲұпјҢеә—иҖҒжқҝжӯЈе°ҶеҲҡеҺӢеҲ¶еҘҪзҡ„иұҶи…җеёғеҢ…иҪ»иҪ»жҺҖејҖпјҢеҸҢжүӢжөёеңЁжҷЁе…үйҮҢпјҢеҠЁдҪңеҲ©иҗҪең°еҲҮзқҖпјҢеғҸеңЁеј№еҘҸзқҖдёҖжһ¶еҸӨзҗҙгҖӮ
еҘ¶зҷҪиүІиў…иў…зҡ„зғӯж°”иЈ№зқҖиҚүжңЁжё…иҠ¬пјҢжҒ°дјјжҳҘйӣҫиҙҙзқҖж№–йқўжёёиө°гҖӮиҝҷиҲ¬еҜ»еёёзҡ„еҗғйЈҹпјҢз«ҹиғҪи®©дәәе“ҒеҮәеҚғе№ҙеүҚзҡ„еҶөе‘і——ж·®еҚ—зҺӢеҲҳе®үеңЁе…«е…¬еұұдёӢзӮјдё№пјҢдё№зӮүйҮҢзҝ»ж¶Ңзҡ„иұҶжөҶеҮқжҲҗзҷҪзҺүпјҢд»ҺжӯӨдәәй—ҙдҫҝеӨҡдәҶиҝҷеҸҜзәізҷҫе‘ізҡ„иҮіжҹ”д№Ӣзү©гҖӮиұҶи…җз”ҹжҖ§жё©ж¶ҰпјҢеҚҙи•ҙи—ҸзқҖжғҠдәәзҡ„еҠӣйҮҸпјҡжҜҸеқ—йӣӘзҷҪж–№еҜёй—ҙпјҢйғҪиң·дјҸзқҖе ӘжҜ”йұјиӮүзҡ„иӣӢзҷҪиҙЁпјҢжІүж·ҖзқҖдёҺзүӣеҘ¶жҜ”иӮ©зҡ„й’ҷиҙЁпјҢжӣҙи—ҸзқҖгҖҠйҪҗж°‘иҰҒжңҜгҖӢйҮҢи®°иҪҪзҡ„“зӣҠж°”е’Ңдёӯ”зҡ„еҸӨиҖҒжҷәж…§гҖӮ
е№Ій»„иұҶз»ҸиҝҮдёҖеӨңзҡ„жөёжіЎпјҢз»„з»Үжҹ”иҪҜпјҢеӨ–еҪўйҘұж»ЎпјҢд»ҺзЈЁзӣҳй—ҙжұ©жұ©жөҒж·ҢеҮәд№іиүІжәӘжөҒпјҢй“Ғй”…иҫ№зҡ„и’ёж°”зғӯзғҲең°еҚҮи…ҫиҖҢиө·пјҢж°Өж°ІдәҶйӮЈйҰ–жіӣй»„зҡ„гҖҠиұҶи…җиҜ—гҖӢпјҡ“з§ҚиұҶиұҶиӢ—зЁҖпјҢеҠӣз«ӯеҝғе·Іи…җгҖӮж—©зҹҘж·®еҚ—жңҜпјҢе®үеқҗиҺ·жіүеёғгҖӮ”зҺ°д»Јз§‘жҠҖдёәеҸӨжі•ж·»дәҶ件й“Ғй“ёзҡ„й“ з”ІпјҢеҚҙжңӘж”№зҹізЈЁиҪ¬еҠЁзҡ„еҸӨиҖҒеҝғи·ігҖӮ
еңЁзҺ°д»ЈзӨҫдјҡпјҢиҷҪ然жңәжў°еҢ–зҡ„з”ҹдә§ж–№ејҸе·Із»ҸеӨ§еӨ§жҸҗй«ҳдәҶж•ҲзҺҮпјҢдҪҶдҪҝз”Ёдј з»ҹе·ҘиүәеҲ¶дҪңзҡ„иұҶи…җд»Қ然被дёҖдәӣдәәдҝқз•ҷе’Ңдј жүҝпјҢе®ғдёҚд»…жҳҜдёҖз§Қз”ҹдә§ж–№ејҸпјҢжӣҙжҳҜдёҖз§Қж–ҮеҢ–зҡ„дҪ“зҺ°гҖӮ
дәҢ
еә—иҖҒжқҝж”ҫе®ҢдёҖй”…иұҶжөҶпјҢжҺўиә«жӢҝзқҖжё…жҙҒзҗғжё…жҙ—й”…еҶ…зҡ„дёҖж №ж №з”өзғӯжЈ’гҖӮи¶ҒзқҖй—ҙйҡҷпјҢжҲ‘дёҺд»–иҒҠиө·жқҘпјҢеә—иҖҒжқҝ姓жқЁпјҢд»Ҡе№ҙ67еІҒпјҢе№ІиҝҷиЎҢе·Іжңүиҝ‘10дёӘе№ҙеӨҙгҖӮ
“дҪ иҝҷд№Ҳжё…жҙ—пјҢеӨҡиҖҪиҜҜе·ҘеӨ«пјҢдёҚеҪұе“Қз…®дёӢдёҖй”…пјҹ”еҗ¬зқҖжҲ‘зҡ„й—®иҜқпјҢжқЁеӨ§е“Ҙе®һиҜҡең°иҜҙпјҡ“жҳҜиҙ№зӮ№еҠӣж°”пјҢеҸҜиҝҷиғҪдҝқжҢҒиұҶжөҶзҡ„еҺҹжұҒеҺҹе‘ігҖӮе№Іиҝҷжҙ»е„ҝпјҢдёҖдёқдёҖжҜ«дёҚ敢马иҷҺгҖӮ”
иұҶжөҶеңЁдёҖзұій«ҳзҡ„еӨ§жЎ¶йҮҢйқҷзҪ®дәҶзүҮеҲ»пјҢжқЁеӨ§е“ҘејҖе§ӢзӮ№иұҶи…җгҖӮеҸӘи§Ғд»–е·ҰжүӢжӢҝ瓶пјҢеҸіжүӢжҢҒе·Ҙе…·ж…ўж…ўжҗ…жӢҢиө·жқҘгҖӮжҲ‘зңӢзқҖеҝғжҖҘпјҢеӮ¬д»–дёҖдёӢеӯҗеҖ’иҝӣеҺ»дёҚеҝ«дәӣпјҹ
“иҝҷеҚӨж°ҙзӮ№иұҶи…җеҸҜжҖҘдёҚеҫ—гҖӮ”жқЁеӨ§е“Ҙзј“зј“з”Ёйқ’зӣҗеҚӨеқҮеҢҖең°зӮ№зқҖпјҢжүӢи…•жӮ¬еңЁеҚҠз©әз”»зқҖеңҶеј§гҖӮ“дҪ зңӢиұҶжөҶеңЁеҸҳеҢ–гҖӮ”жқЁеӨ§е“ҘиҜқиЁҖжңӘиҗҪпјҢжЎ¶йҮҢеҫ®еҫ®йўӨеҠЁзҡ„иұҶжөҶпјҢжёҗжёҗеҮқжҲҗзө®зҠ¶зҡ„дә‘еӣўгҖӮзңҹжҳҜ“дё–з•ҢзңҹеҘҮеҰҷпјҢдёҚзңӢдёҚзҹҘйҒ“”гҖӮ
и®°еҫ—жқҺж—¶зҸҚеңЁгҖҠжң¬иҚүзәІзӣ®гҖӢйҮҢеҶҷйҒ“пјҡ“иұҶи…җд№Ӣжі•пјҢе§ӢдәҺжұүж·®еҚ—зҺӢгҖӮеҮЎй»‘иұҶгҖҒй»„иұҶеҸҠзҷҪиұҶгҖҒз»ҝиұҶд№Ӣзұ»пјҢзҡҶеҸҜдёәд№ӢгҖӮ”жӯӨеҲ»пјҢзһ…зқҖжқЁеӨ§е“Ҙе°ҶеӨ§жЎ¶йҮҢзҡ„дә‘зө®иҲҖиҝӣзІ—еёғеҢ…йҮҢпјҢеҖ’еғҸжҳҜжҠҠж•ҙзүҮжұүж—¶жңҲиүІйғҪ收иҝӣдәҶжЈүзәұз»Ҹзә¬гҖӮд»–еҰ»еӯҗж“ҚдҪңзқҖиҮӘеҠЁеҺӢжҰЁжңәпјҢдёҚй”Ҳй’ўеҷЁжў°дёҺеҘ№жңүеҠӣзҡ„жүӢжҺҢй»ҳеҘ‘еҗҲеҘҸпјҢдј з»ҹдёҺзҺ°д»ЈеңЁжҷЁе…үдёӯиҫҫжҲҗеҫ®еҰҷзҡ„е’Ңи§ЈгҖӮ
жЎҲеҸ°дёҠдёҖжқҝжқҝжё©зғӯзҡ„иұҶи…җеқ—пјҢеҲҮйқўжіӣзқҖиұЎзүҷиҲ¬зҡ„е…үжіҪпјҢиў«йЎҫе®ўдёҖеқ—еқ—ең°д№°иө°гҖӮдёҚи§үй—ҙпјҢи®©жҲ‘жғіиө·йҷҶжёё“ж—ӢеҺӢй»ҺзҘҒиҪҜиғңй…Ҙ”зҡ„иҜ—еҸҘгҖӮжқЁеӨ§е“Ҙзҡ„еҰ»еӯҗйҖ’жқҘеҚҠзў—иұҶжөҶпјҢдёҖзңӢе°ұжҜ”еҜ»еёёзҡ„иұҶжөҶжө“зЁ дёүеҲҶгҖӮиҪ»жҠҝдёҖеҸЈпјҢеҲқе…ҘеҸЈж—¶еҰӮдёқз»ёжӢӮиҝҮе”ҮйҪҝпјҢ继иҖҢйҶҮеҺҡзҡ„иұҶйҰҷеңЁеҸЈи…”иҪ°з„¶з»Ҫж”ҫпјҢд»ҝиӢҘеҚғдёҮйў—й»„иұҶеҗҢж—¶зӮёејҖйҮ‘й»„зҡ„й“ з”ІпјҢе°Ҷиҙ®еӯҳдёүеӯЈзҡ„йҳіе…үеҖҫжі»иҖҢеҮәгҖӮз»Ҷе“Ғж—¶еҸҲжңүеӣһз”ҳпјҢдјјжңүиҝҳж— зҡ„жё…з”ңеңЁе–үеӨҙжү“зқҖж—Ӣе„ҝпјҢи®©дәәжғіиө·з§Ӣ收时иҠӮиұҶиҚҡиЈӮејҖзҡ„еҷје•ӘеЈ°гҖӮ
жҲ‘еҝҪең°и§үеҫ—е№іж—¶д№°зҡ„иұҶи…җжҜ”иҝҷ家зҡ„дҫҝе®ңпјҢдҫҝеҝғз”ҹз–‘зӘҰгҖӮжқЁеӨ§е“Ҙи§ЈйҮҠйҒ“пјҡ“зҹіиҶҸзӮ№еҲ¶зҡ„иұҶи…җеҮәеҫ—еӨҡпјҢжҲ‘иҝҷеҚӨж°ҙиҖҒжі•еӯҗзӮ№еҲ¶зҡ„иұҶи…җиҰҒе°‘дёҖеҚҠиҝҳеӨҡгҖӮ”еҷўпјҢеҺҹжқҘеҰӮжӯӨпјҢжһңзңҹеә”йӘҢ“дёҖеҲҶд»·й’ұдёҖеҲҶиҙ§”зҡ„иҖҒиҜқгҖӮ
жқЁеӨ§е“ҘжҺҖејҖиҝҳеҶ’зқҖзғӯж°”зҡ„иұҶи…җеҢ…пјҢйӣӘзҷҪзҡ„иЎЁйқўдёҠеёғж»Ўз»ҶеҜҶеӯ”жҙһпјҢе®ӣеҰӮжңҲйқўзҺҜеҪўеұұгҖӮиҝҷжҳҜж—¶й—ҙдёҺеҠӣйҒ“е…ұеҗҢйӣ•еҲ»зҡ„зә№з« пјҢжҜҸдёӘж°”еӯ”йғҪжҳҜеӨ§иұҶзәӨз»ҙдёҺзӣҗеҚӨеҜ№иҜқзҡ„йҒ—иҝ№гҖӮз«№зӯҗйҮҢиң·жӣІзҡ„иұҶиҠҪзӘҒ然еҸ‘еҮәз»ҶзўҺе“ҚеҠЁпјҢеҺҹжҳҜж°ҙзҸ йЎәзқҖиҠҪе°–еқ иҗҪпјҢеңЁжҷЁе…үйҮҢдёІжҲҗжҷ¶дә®зҡ„зҸ й“ҫгҖӮиҝҷи®©жҲ‘еҝҶиө·иўҒжһҡеңЁгҖҠйҡҸеӣӯйЈҹеҚ•гҖӢйҮҢиҜҙзҡ„“иұҶи…җеҫ—е‘іпјҢиҝңиғңзҮ•зӘқ”пјҢжӯӨж—¶ж–№зҹҘиҜҡдёҚжҲ‘ж¬әгҖӮ
“з”Ёйқ’зӣҗеҚӨж°ҙзӮ№еҲ¶зҡ„иұҶи…җпјҢиҙЁең°зҙ§еҜҶпјҢеҸЈж„ҹзӯӢйҒ“пјҢиұҶйҰҷжө“йғҒгҖӮдёҚдҝЎпјҢдҪ е°қе°қгҖӮ”жқЁеӨ§е“ҘиҜҙгҖӮ
дёү
гҖҠеҗҺжұүд№Ұ·еҚ·дәҢеҚҒеӣӣ·й©¬жҸҙдј гҖӢиҪҪпјҢ马жҸҙеҪ“ж—¶е·Із»Ҹ62еІҒпјҢжұүе…үжӯҰеёқеҲҳз§ҖжӢ…еҝғд»–зҡ„иә«дҪ“пјҢдёҚж„ҝж„Ҹи®©д»–еҮәжҲҳгҖӮ马жҸҙеҲҷиҮӘдҝЎең°иЎЁзӨәиҮӘе·ұд»Қ然иғҪжҠ«з”ІдёҠ马пјҢдәҺжҳҜеҲҳз§Җи®©д»–иҜ•дёҖиҜ•гҖӮ马жҸҙи·ЁдёҠйӣ•йһҚпјҢзҘһйҮҮеҘ•еҘ•ең°зҺҜи§Ҷеӣӣе‘ЁпјҢд»ҘзӨәеҸҜз”ЁгҖӮеҲҳз§Җи§ҒзҠ¶з¬‘йҒ“пјҡ“зҹҚй“„е“үпјҢжҳҜзҝҒд№ҹпјҒ”зІҫзҘһзҹҚй“„ж„ҸжҢҮиҖҒдәәеҜҢжңүзІҫзҘһпјҢиҖҒиҖҢејәеҒҘпјҢдёҚеӨұйЈҺйҮҮгҖӮиҝҷдёӘжҲҗиҜӯж”ҫеңЁзІҫзҘһеҒҘж—әзҡ„жқЁеӨ§е“Ҙиә«дёҠеҶҚжҒ°её–дёҚиҝҮдәҶгҖӮ
зІҫзҘһзҹҚй“„зҡ„жқЁеӨ§е“ҘпјҢе№Іиө·жҙ»жқҘж—ўйә»еҲ©еҸҲдәўеҘӢпјҢдёқжҜ«зңӢдёҚеҮәд»–е·ІжҳҜ“еҘ”дёғ”зҡ„дәәдәҶгҖӮеҲҳз§ҖиӢҘзңӢеҲ°д»–зҡ„еҠІеӨҙпјҢдёҚзҹҘиҰҒжҖҺд№ҲеӨёе‘ўпјҒ
жқЁеӨ§е“ҘжҜҸеӨ©4ж—¶еҮҶзӮ№жқҘеҲ°иұҶи…җеқҠпјҢејҖе§ӢжҢүйғЁе°ұзҸӯзҡ„еҝҷзўҢгҖӮд»–е…Ҳе°ҶеүҚдёҖеӨ©еӨңйҮҢжіЎеҘҪзҡ„й»„иұҶзІүзўҺпјҢ然еҗҺз»ҸиҝҮиҝҮж»ӨгҖҒз…®зҶҹгҖҒйқҷзҪ®гҖҒзӮ№еҚӨпјҢжңҖеҗҺеҺӢеҲ¶жҲҗеһӢгҖӮжҜҸеӨ©еҰӮжӯӨпјҢиҠӮеҒҮж—ҘдјҡжӣҙиҫӣиӢҰдәӣгҖӮжҲ‘зңӢеҲ°еҚ—еўҷдёҠй»„еә•з»ҝеӯ—йҶ’зӣ®зҡ„ж ҮиҜӯпјҡдёҚдҪҝз”ЁйҳІи…җж·»еҠ еүӮпјҢдёҚдҪҝз”ЁиҪ¬еҹәеӣ еӨ§иұҶгҖӮиҜҙеҲ°еҒҡеҲ°пјҢйҡҫжҖӘеҗёеј•иҝҷд№ҲеӨҡеӣһеӨҙе®ўгҖӮжҲ‘дёҚзҰҒи„ұеҸЈиөһйҒ“пјҡ“дҪ иҝҷеҸҜжҳҜз„ҰдҪңзҡ„‘иғ–дёңжқҘ’е•ҠпјҒ”
“д»–еҒҡзҡ„иұҶи…җзЎ®е®һеҫҲиүҜеҝғгҖӮ”жҺҘжҲ‘иҜқзҡ„жҳҜдёҖдҪҚеҒҘеЈ®дҪ“ж јзҡ„дёӯе№ҙз”·еӯҗгҖӮеҜ№ж–№з»ҷжҲ‘д»Ӣз»ҚпјҢд»–иҖ„иҖӢд№Ӣе№ҙзҡ„иҖҒжҜҚдәІеҺҹе…ҲдҪҸеңЁеёӮйҫҷжәҗж№–е…¬еӣӯйҷ„иҝ‘пјҢе°ұе–ңж¬ўеҗғиҝҷ家зҡ„иұҶи…җпјҢеҺ»е№ҙжҗ¬еҲ°зјқеұұе…¬еӣӯйҷ„иҝ‘еұ…дҪҸпјҢиҝҳеҝөеҸҠиҝҷйҮҢзҡ„иұҶи…җпјҢд»–дҫҝжҜҸеӨ©з”ұеҢ—еҲ°еҚ—з©ҝеҹҺиҖҢиҝҮпјҢи·‘е°Ҷиҝ‘10е…¬йҮҢең°жқҘиҝҷе„ҝд№°дёҠеҮ еқ—иұҶи…җгҖӮиҝҷйҮҢзҡ„иұҶи…җиҷҪ然иҙөдәӣпјҢеҸҜеҗғзқҖж”ҫеҝғпјҢеҗғзқҖиҲ’еҝғгҖӮ
дҪ•жӯўжҳҜиҖҒеӨӘеӨӘеҝөеҸҠиҝҷиҮӘзЈЁиұҶи…җпјҢжқЁеӨ§е“ҘиҜҙдёҖдәӣеҚ–зғӯиұҶи…җе’ҢзғӯиұҶиҠұзҡ„з»ҸиҗҘиҖ…йғҪжқҘд»–иҝҷйҮҢжӢҝиҙ§гҖӮеҪ’йҖ”пјҢйӮӮйҖ…д»Һиҝҷ家иұҶи…җеқҠиҝӣиҙ§зҡ„дёӘдҪ“з»ҸиҗҘиҖ…еңЁеҚ–иұҶи…җи„‘гҖӮжңЁжЎ¶жҸӯејҖж—¶пјҢйӣӘзҷҪзҡ„иұҶи…җи„‘йўӨе·Қе·Қжҳ зқҖеӨ©е…үпјҢжөҮдёҠиҷҫзұҪгҖҒй…ұжІ№пјҢж’’дёҠзӮ№зў§з»ҝзҡ„иҠ«иҚҪжң«пјҢеҖ’еғҸжҳҜжҠҠжұҹеҚ—зғҹйӣЁйғҪзӣӣеңЁдәҶзІ—з“·зў—дёӯгҖӮеҚіеҲ»жғіиө·жңұзҶ№еҶҷиұҶи…җзҡ„иҜ—еҸҘпјҡ“ж—©зҹҘж·®еҚ—жңҜпјҢе®үеқҗиҺ·жіүеёғгҖӮ”еҝҪ然жҮӮеҫ—иҝҷеҜ»еёёйЈҹзү©йҮҢи—ҸзқҖзҡ„пјҢеҺҹжҳҜдёӯеӣҪдәәеҚғе№ҙжқҘеҜ№еңҹең°зҡ„зң·жҒӢгҖӮиұҶи…җи„‘ж»‘иҝҮиҲҢе°–зҡ„еҲ№йӮЈпјҢз»Ҷи…»еҰӮеҗ»зҡ„и§Ұж„ҹйҮҢпјҢеҲҶжҳҺиғҪе°қеҮәй»‘еңҹең°йҮҢй’ҷиҙЁзҡ„жё…еҶҪгҖҒеӨ§иұҶејӮй»„й…®зҡ„жё©еӯҳд»ҘеҸҠжӨҚзү©иӣӢзҷҪеңЁе”ҮйҪҝй—ҙжё©жҹ”зҡ„зҲҶз ҙгҖӮ
иҲҖдёҖеӢәйҖҒе…ҘеҳҙдёӯпјҢж»‘зҲҪжҹ”е«©зҡ„еҸЈж„ҹпјҢи®©дәәжғіиө·еҚ—е®Ӣж—¶жңҹжһ—жҙӘжүҖи‘—зҡ„йҘ®йЈҹ笔记гҖҠеұұ家清дҫӣгҖӢйҮҢи®°иҪҪзҡ„“йӣӘйңһзҫ№”——иұҶи…җдёҺиҠҷи“үиҠұеҗҢз…®пјҢзҷҪйҮҢйҖҸзәўеҰӮйӣӘжҳ йңһе…үгҖӮиҝҷж—¶иҷҪж— иҠҷи“үпјҢдҪҶжҳҘйҹӯеҲҮзўҺжӢҢзқҖе«©иұҶи…җпјҢйқ’зҷҪзӣёй—ҙпјҢеҖ’еә”дәҶеҸӨдәә“йҮ‘жЁҪзҺүж¶ІдёҚи¶іиҙөпјҢиұҶи…җйқ’иҸңдҝқе№іе®ү”зҡ„дҝҡиҜӯгҖӮиұҶи…җеңЁйҪҝй—ҙзўҺиЈӮж—¶пјҢеӨ§иұҶеҚөзЈ·и„Ӯзҡ„иҠ¬иҠідёҺз»ҙз”ҹзҙ Eзҡ„ж¶ҰжіҪпјҢжӯЈжӮ„жӮ„жҠҡе№ізҺ°д»Јдәәз„Ұиҷ‘зҡ„иӮ иғғгҖӮ
йӮЈдәӣзҹізЈЁиҪ¬еҠЁзҡ„еҗұе‘ҖеЈ°пјҢеҚӨж°ҙж»ҙиҗҪзҡ„еҸ®е’ҡеЈ°пјҢиҝҳжңүжҷЁйӣҫйҮҢжӯӨиө·еҪјдјҸзҡ„“иұҶи…җ……”зҡ„еҗҶе–қеЈ°пјҢеҺҹжқҘйғҪжҳҜеҸӨиҖҒж–ҮжҳҺз»ө延иҮід»Ҡзҡ„йҹөи„ҡгҖӮжҺ’йҳҹзҡ„дәәзҫӨдёӯпјҢжңүе№ҙиҪ»жҜҚдәІеҝөеҸЁзқҖ“йӣ¶ж·»еҠ ”пјҢжңүиҖҒиҖ…ж„ҹж…Ё“иҝҷжүҚжҳҜиұҶи…җиҜҘжңүзҡ„жЁЎж ·”пјҢжҜҸдёӘдәәзҡ„и§ӮеҝөйҮҢпјҢйғҪзӣӣзқҖеҜ№жҠ—е·ҘдёҡжҙӘжөҒзҡ„еҫ®и–„дҝЎеҝөгҖӮ
иұҶзІ’еҗёйҘұдәҶжңҲиүІпјҢйқҷйқҷзӯүеҫ…ж–°дёҖиҪ®иҪ®еӣһгҖӮиҝҷиұҶи…җйҰҷгҖҒиұҶжөҶжө“зҡ„дәәй—ҙзғҹзҒ«пјҢз»Ҳе°ҶиҰҒзҢ®з»ҷеӨ§ең°пјҢеҶҷз»ҷеІҒжңҲгҖӮ
жҳҜе•ҠпјҢдәә们иҙӯд№°зҡ„дёҚд»…жҳҜиӣӢзҷҪиҙЁдёҺй’ҷиҙЁзҡ„з»“еҗҲдҪ“пјҢжӣҙжҳҜзҹізЈЁдёҺеҚӨж°ҙзҡ„еҸӨиҖҒзӣҹзәҰпјӣдәә们еҗһе’Ҫзҡ„дёҚжӯўжҳҜйҰҷжө“ж»Ӣе‘іпјҢжӣҙжҳҜеңЁдёәеҚіе°Ҷж¶ҲйҖқзҡ„жүӢиүәз»ӯе‘ҪгҖӮ
жқЁеӨ§е“ҘжЎҲжқҝдёҠзҡ„жҜҸдёҖйҒ“еҲ»з—•пјҢйғҪи®°еҪ•зқҖзҺ°д»ЈдәәеҜ№жң¬зңҹзҡ„жёҙжңӣ——еңЁиҝҷиў«еҢ–еӯҰж–№зЁӢејҸз»ҹжІ»зҡ„жҳҹзҗғдёҠпјҢжҖ»иҜҘз•ҷдәӣж»ҡзғ«зҡ„иұҶжөҶпјҢеӣәжү§ең°жІҝзқҖйҷ¶зў—иҫ№зјҳпјҢжј«еҮәд№ізҷҪиүІзҡ„гҖҒеҶ’зқҖзғӯж°”зҡ„иҜ—иЎҢгҖӮ

 иұ«ICPеӨҮ14012713еҸ·
еӨҮжЎҲ/и®ёеҸҜиҜҒеҸ·пјҡиұ«ICPеӨҮ14012713еҸ·-1
иұ«ICPеӨҮ14012713еҸ·
еӨҮжЎҲ/и®ёеҸҜиҜҒеҸ·пјҡиұ«ICPеӨҮ14012713е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