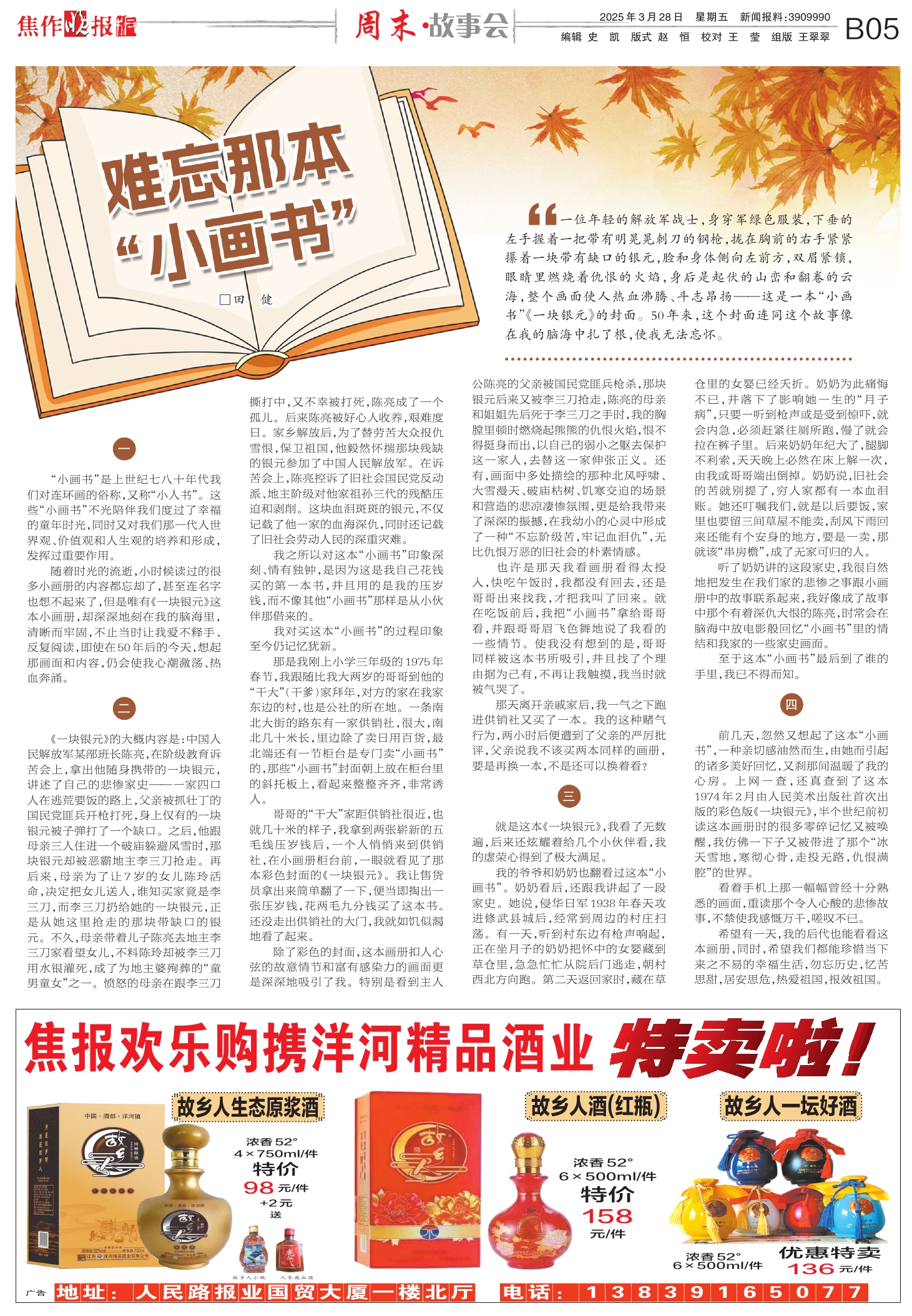内容详情
2025年03月28日
难忘那本“小画书”
□田 健
一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身穿军绿色服装,下垂的左手握着一把带有明晃晃刺刀的钢枪,拢在胸前的右手紧紧攥着一块带有缺口的银元,脸和身体侧向左前方,双眉紧锁,眼睛里燃烧着仇恨的火焰,身后是起伏的山峦和翻卷的云海,整个画面使人热血沸腾、斗志昂扬——这是一本“小画书”《一块银元》的封面。50年来,这个封面连同这个故事像在我的脑海中扎了根,使我无法忘怀。
一
“小画书”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对连环画的俗称,又称“小人书”。这些“小画书”不光陪伴我们度过了幸福的童年时光,同时又对我们那一代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培养和形成,发挥过重要作用。
随着时光的流逝,小时候读过的很多小画册的内容都忘却了,甚至连名字也想不起来了,但是唯有《一块银元》这本小画册,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而牢固,不止当时让我爱不释手、反复阅读,即使在50年后的今天,想起那画面和内容,仍会使我心潮激荡、热血奔涌。
二
《一块银元》的大概内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班长陈亮,在阶级教育诉苦会上,拿出他随身携带的一块银元,讲述了自己的悲惨家史——一家四口人在逃荒要饭的路上,父亲被抓壮丁的国民党匪兵开枪打死,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被子弹打了一个缺口。之后,他跟母亲三人住进一个破庙躲避风雪时,那块银元却被恶霸地主李三刀抢走。再后来,母亲为了让7岁的女儿陈玲活命,决定把女儿送人,谁知买家竟是李三刀,而李三刀扔给她的一块银元,正是从她这里抢走的那块带缺口的银元。不久,母亲带着儿子陈亮去地主李三刀家看望女儿,不料陈玲却被李三刀用水银灌死,成了为地主婆殉葬的“童男童女”之一。愤怒的母亲在跟李三刀撕打中,又不幸被打死,陈亮成了一个孤儿。后来陈亮被好心人收养,艰难度日。家乡解放后,为了替劳苦大众报仇雪恨,保卫祖国,他毅然怀揣那块残缺的银元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诉苦会上,陈亮控诉了旧社会国民党反动派、地主阶级对他家祖孙三代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块血泪斑斑的银元,不仅记载了他一家的血海深仇,同时还记载了旧社会劳动人民的深重灾难。
我之所以对这本“小画书”印象深刻、情有独钟,是因为这是我自己花钱买的第一本书,并且用的是我的压岁钱,而不像其他“小画书”那样是从小伙伴那借来的。
我对买这本“小画书”的过程印象至今仍记忆犹新。
那是我刚上小学三年级的1975年春节,我跟随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到他的“干大”(干爹)家拜年,对方的家在我家东边的村,也是公社的所在地。一条南北大街的路东有一家供销社,很大,南北几十米长,里边除了卖日用百货,最北端还有一节柜台是专门卖“小画书”的,那些“小画书”封面朝上放在柜台里的斜托板上,看起来整整齐齐,非常诱人。
哥哥的“干大”家距供销社很近,也就几十米的样子,我拿到两张崭新的五毛线压岁钱后,一个人悄悄来到供销社,在小画册柜台前,一眼就看见了那本彩色封面的《一块银元》。我让售货员拿出来简单翻了一下,便当即掏出一张压岁钱,花两毛九分钱买了这本书。还没走出供销社的大门,我就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
除了彩色的封面,这本画册扣人心弦的故意情节和富有感染力的画面更是深深地吸引了我。特别是看到主人公陈亮的父亲被国民党匪兵枪杀,那块银元后来又被李三刀抢走,陈亮的母亲和姐姐先后死于李三刀之手时,我的胸膛里顿时燃烧起熊熊的仇恨火焰,恨不得挺身而出,以自己的弱小之躯去保护这一家人,去替这一家伸张正义。还有,画面中多处描绘的那种北风呼啸、大雪漫天、破庙枯树、饥寒交迫的场景和营造的悲凉凄惨氛围,更是给我带来了深深的振撼,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形成了一种“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无比仇恨万恶的旧社会的朴素情感。
也许是那天我看画册看得太投入,快吃午饭时,我都没有回去,还是哥哥出来找我,才把我叫了回来。就在吃饭前后,我把“小画书”拿给哥哥看,并跟哥哥眉飞色舞地说了我看的一些情节。使我没有想到的是,哥哥同样被这本书所吸引,并且找了个理由据为己有,不再让我触摸,我当时就被气哭了。
那天离开亲戚家后,我一气之下跑进供销社又买了一本。我的这种赌气行为,两小时后便遭到了父亲的严厉批评,父亲说我不该买两本同样的画册,要是再换一本,不是还可以换着看?
三
就是这本《一块银元》,我看了无数遍,后来还炫耀着给几个小伙伴看,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
我的爷爷和奶奶也翻看过这本“小画书”。奶奶看后,还跟我讲起了一段家史。她说,侵华日军1938年春天攻进修武县城后,经常到周边的村庄扫荡。有一天,听到村东边有枪声响起,正在坐月子的奶奶把怀中的女婴藏到草仓里,急急忙忙从院后门逃走,朝村西北方向跑。第二天返回家时,藏在草仓里的女婴已经夭折。奶奶为此痛悔不已,并落下了影响她一生的“月子病”,只要一听到枪声或是受到惊吓,就会内急,必须赶紧往厕所跑,慢了就会拉在裤子里。后来奶奶年纪大了,腿脚不利索,天天晚上必然在床上解一次,由我或哥哥端出倒掉。奶奶说,旧社会的苦就别提了,穷人家都有一本血泪账。她还叮嘱我们,就是以后要饭,家里也要留三间草屋不能卖,刮风下雨回来还能有个安身的地方,要是一卖,那就该“串房檐”,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听了奶奶讲的这段家史,我很自然地把发生在我们家的悲惨之事跟小画册中的故事联系起来,我好像成了故事中那个有着深仇大恨的陈亮,时常会在脑海中放电影般回忆“小画书”里的情结和我家的一些家史画面。
至于这本“小画书”最后到了谁的手里,我已不得而知。
四
前几天,忽然又想起了这本“小画书”,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由她而引起的诸多美好回忆,又刹那间温暖了我的心房。上网一查,还真查到了这本1974年2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首次出版的彩色版《一块银元》,半个世纪前初读这本画册时的很多零碎记忆又被唤醒,我仿佛一下子又被带进了那个“冰天雪地,寒彻心骨,走投无路,仇恨满腔”的世界。
看着手机上那一幅幅曾经十分熟悉的画面,重读那个令人心酸的悲惨故事,不禁使我感慨万千,嗟叹不已。
希望有一天,我的后代也能看看这本画册,同时,希望我们都能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勿忘历史,忆苦思甜,居安思危,热爱祖国,报效祖国。
 豫ICP备14012713号
备案/许可证号:豫ICP备14012713号-1
豫ICP备14012713号
备案/许可证号:豫ICP备14012713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