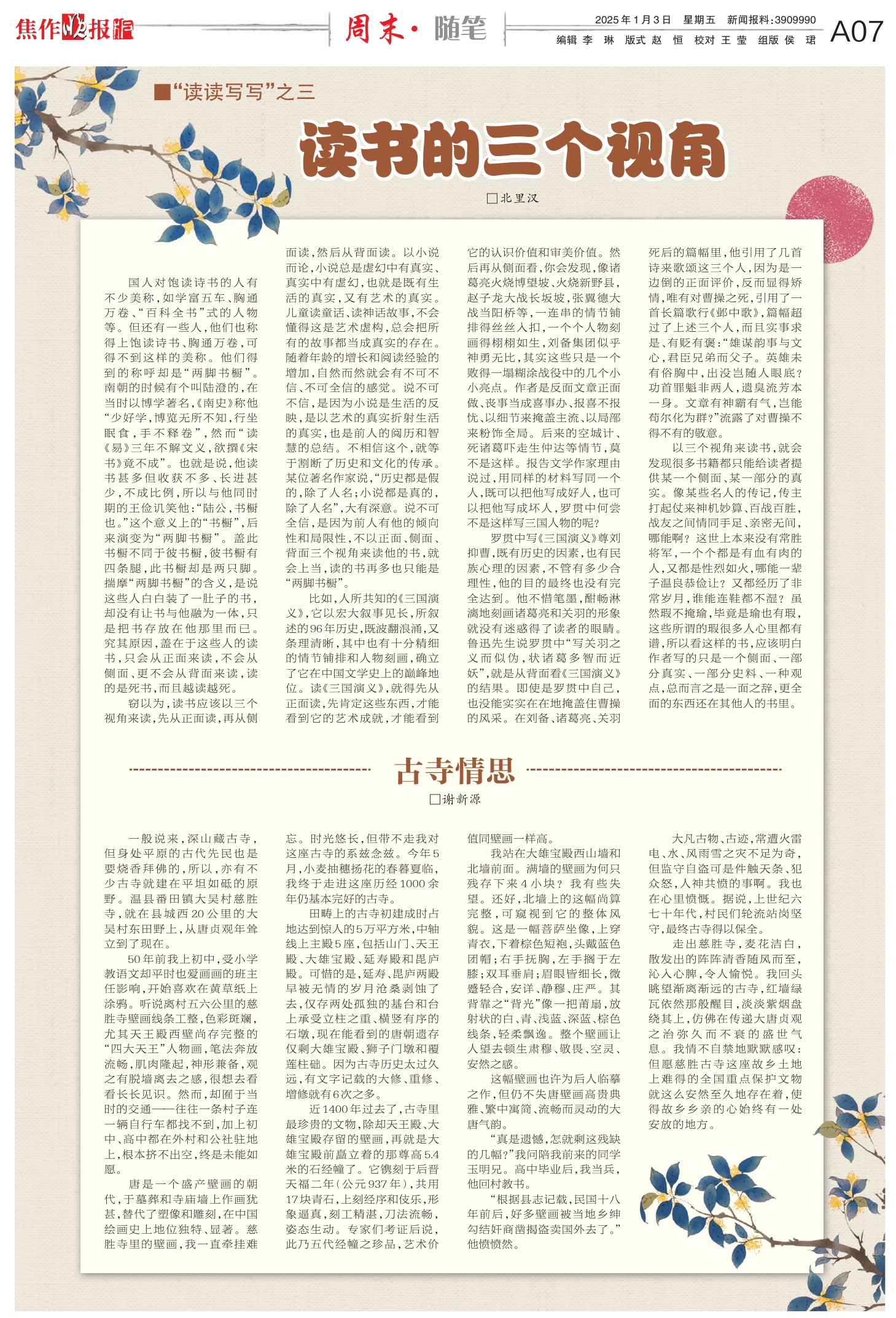内容详情
2025年01月03日
■“读读写写”之三
读书的三个视角
□ 北里汉
国人对饱读诗书的人有不少美称,如学富五车、胸通万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等。但还有一些人,他们也称得上饱读诗书、胸通万卷,可得不到这样的美称。他们得到的称呼却是“两脚书橱”。南朝的时候有个叫陆澄的,在当时以博学著名,《南史》称他“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然而“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也就是说,他读书甚多但收获不多、长进甚少,不成比例,所以与他同时期的王俭讥笑他:“陆公,书橱也。”这个意义上的“书橱”,后来演变为“两脚书橱”。盖此书橱不同于彼书橱,彼书橱有四条腿,此书橱却是两只脚。揣摩“两脚书橱”的含义,是说这些人白白装了一肚子的书,却没有让书与他融为一体,只是把书存放在他那里而已。究其原因,盖在于这些人的读书,只会从正面来读,不会从侧面、更不会从背面来读,读的是死书,而且越读越死。
窃以为,读书应该以三个视角来读,先从正面读,再从侧面读,然后从背面读。以小说而论,小说总是虚幻中有真实、真实中有虚幻,也就是既有生活的真实,又有艺术的真实。儿童读童话、读神话故事,不会懂得这是艺术虚构,总会把所有的故事都当成真实的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读经验的增加,自然而然就会有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的感觉。说不可不信,是因为小说是生活的反映,是以艺术的真实折射生活的真实,也是前人的阅历和智慧的总结。不相信这个,就等于割断了历史和文化的传承。某位著名作家说,“历史都是假的,除了人名;小说都是真的,除了人名”,大有深意。说不可全信,是因为前人有他的倾向性和局限性,不以正面、侧面、背面三个视角来读他的书,就会上当,读的书再多也只能是“两脚书橱”。
比如,人所共知的《三国演义》,它以宏大叙事见长,所叙述的96年历史,既波翻浪涌,又条理清晰,其中也有十分精细的情节铺排和人物刻画,确立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巅峰地位。读《三国演义》,就得先从正面读,先肯定这些东西,才能看到它的艺术成就,才能看到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然后再从侧面看,你会发现,像诸葛亮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县,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张翼德大战当阳桥等,一连串的情节铺排得丝丝入扣,一个个人物刻画得栩栩如生,刘备集团似乎神勇无比,其实这些只是一个败得一塌糊涂战役中的几个小小亮点。作者是反面文章正面做、丧事当成喜事办、报喜不报忧、以细节来掩盖主流、以局部来粉饰全局。后来的空城计、死诸葛吓走生仲达等情节,莫不是这样。报告文学作家理由说过,用同样的材料写同一个人,既可以把他写成好人,也可以把他写成坏人,罗贯中何尝不是这样写三国人物的呢?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尊刘抑曹,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民族心理的因素,不管有多少合理性,他的目的最终也没有完全达到。他不惜笔墨,酣畅淋漓地刻画诸葛亮和关羽的形象就没有迷惑得了读者的眼睛。鲁迅先生说罗贯中“写关羽之义而似伪,状诸葛多智而近妖”,就是从背面看《三国演义》的结果。即使是罗贯中自己,也没能实实在在地掩盖住曹操的风采。在刘备、诸葛亮、关羽死后的篇幅里,他引用了几首诗来歌颂这三个人,因为是一边倒的正面评价,反而显得矫情,唯有对曹操之死,引用了一首长篇歌行《邺中歌》,篇幅超过了上述三个人,而且实事求是、有贬有褒:“雄谋韵事与文心,君臣兄弟而父子。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功首罪魁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流露了对曹操不得不有的敬意。
以三个视角来读书,就会发现很多书籍都只能给读者提供某一个侧面、某一部分的真实。像某些名人的传记,传主打起仗来神机妙算、百战百胜,战友之间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哪能啊?这世上本来没有常胜将军,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的人,又都是性烈如火,哪能一辈子温良恭俭让?又都经历了非常岁月,谁能连鞋都不湿?虽然瑕不掩瑜,毕竟是瑜也有瑕,这些所谓的瑕很多人心里都有谱,所以看这样的书,应该明白作者写的只是一个侧面、一部分真实、一部分史料、一种观点,总而言之是一面之辞,更全面的东西还在其他人的书里。
 豫ICP备14012713号
备案/许可证号:豫ICP备14012713号-1
豫ICP备14012713号
备案/许可证号:豫ICP备14012713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