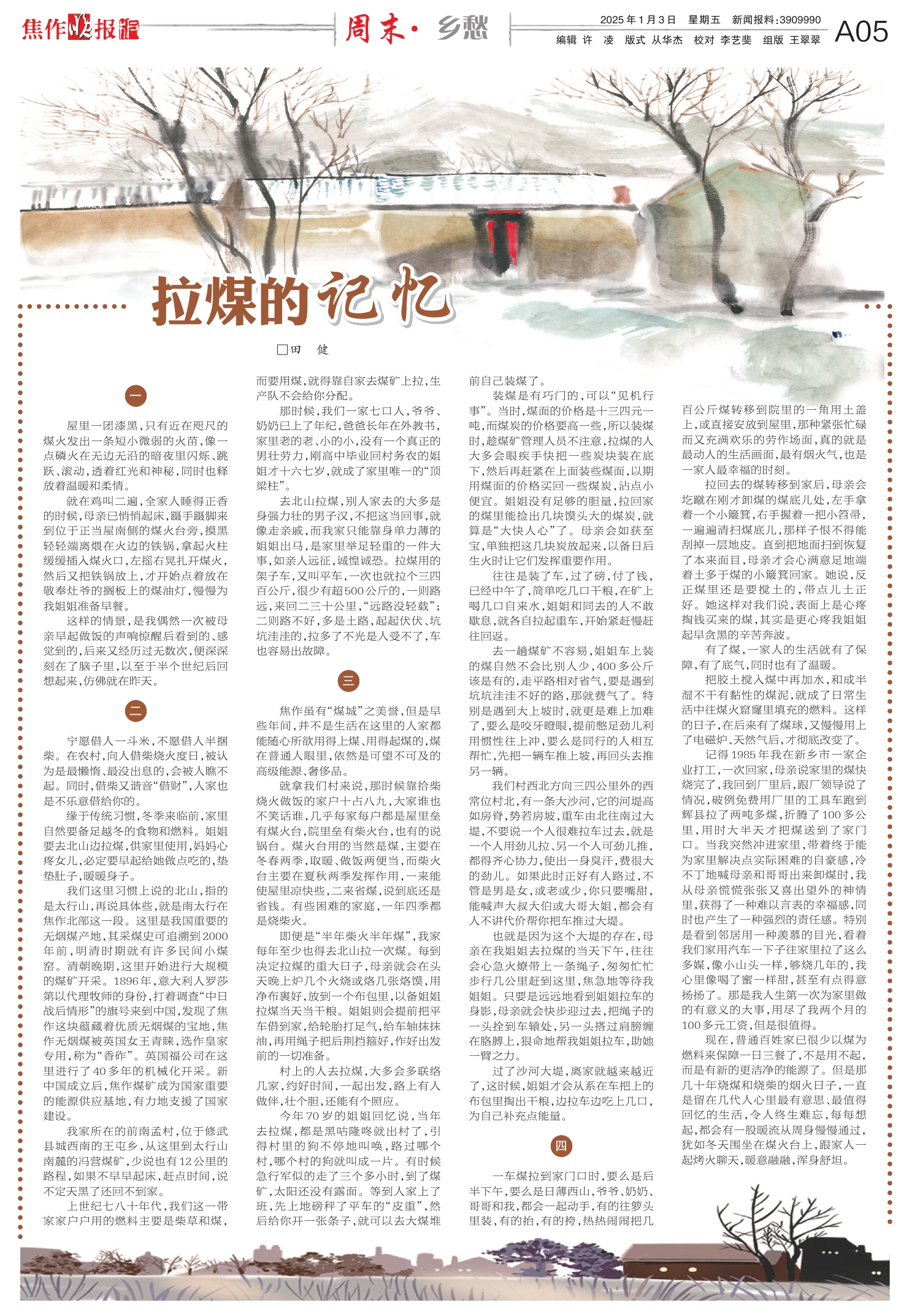内容详情
2025年01月03日
拉煤的记忆
□田 健

一
屋里一团漆黑,只有近在咫尺的煤火发出一条短小微弱的火苗,像一点磷火在无边无沿的暗夜里闪烁、跳跃、滚动,透着红光和神秘,同时也释放着温暖和柔情。
就在鸡叫二遍,全家人睡得正香的时候,母亲已悄悄起床,蹑手蹑脚来到位于正当屋南侧的煤火台旁,摸黑轻轻端离煨在火边的铁锅,拿起火柱缓缓插入煤火口,左摇右晃扎开煤火,然后又把铁锅放上,才开始点着放在敬奉灶爷的搁板上的煤油灯,慢慢为我姐姐准备早餐。
这样的情景,是我偶然一次被母亲早起做饭的声响惊醒后看到的、感觉到的,后来又经历过无数次,便深深刻在了脑子里,以至于半个世纪后回想起来,仿佛就在昨天。
二
宁愿借人一斗米,不愿借人半捆柴。在农村,向人借柴烧火度日,被认为是最懒惰、最没出息的,会被人瞧不起。同时,借柴又谐音“借财”,人家也是不乐意借给你的。
缘于传统习惯,冬季来临前,家里自然要备足越冬的食物和燃料。姐姐要去北山边拉煤,供家里使用,妈妈心疼女儿,必定要早起给她做点吃的,垫垫肚子,暖暖身子。
我们这里习惯上说的北山,指的是太行山,再说具体些,就是南太行在焦作北部这一段。这里是我国重要的无烟煤产地,其采煤史可追溯到2000年前,明清时期就有许多民间小煤窑。清朝晚期,这里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煤矿开采。1896年,意大利人罗莎第以代理牧师的身份,打着调查“中日战后情形”的旗号来到中国,发现了焦作这块蕴藏着优质无烟煤的宝地,焦作无烟煤被英国女王青睐,选作皇家专用,称为“香砟”。英国福公司在这里进行了40多年的机械化开采。新中国成立后,焦作煤矿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供应基地,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建设。
我家所在的前南孟村,位于修武县城西南的王屯乡,从这里到太行山南麓的冯营煤矿,少说也有12公里的路程,如果不早早起床,赶点时间,说不定天黑了还回不到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这一带家家户户用的燃料主要是柴草和煤,而要用煤,就得靠自家去煤矿上拉,生产队不会给你分配。
那时候,我们一家七口人,爷爷、奶奶已上了年纪,爸爸长年在外教书,家里老的老、小的小,没有一个真正的男壮劳力,刚高中毕业回村务农的姐姐才十六七岁,就成了家里唯一的“顶梁柱”。
去北山拉煤,别人家去的大多是身强力壮的男子汉,不把这当回事,就像走亲戚,而我家只能靠身单力薄的姐姐岀马,是家里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如亲人远征,诚惶诚恐。拉煤用的架子车,又叫平车,一次也就拉个三四百公斤,很少有超500公斤的,一则路远,来回二三十公里,“远路没轻载”;二则路不好,多是土路,起起伏伏、坑坑洼洼的,拉多了不光是人受不了,车也容易出故障。
三
焦作虽有“煤城”之美誉,但是早些年间,并不是生活在这里的人家都能随心所欲用得上煤、用得起煤的,煤在普通人眼里,依然是可望不可及的高级能源、奢侈品。
就拿我们村来说,那时候靠拾柴烧火做饭的家户十占八九,大家谁也不笑话谁,几乎每家每户都是屋里垒有煤火台,院里垒有柴火台,也有的说锅台。煤火台用的当然是煤,主要在冬春两季,取暖、做饭两便当,而柴火台主要在夏秋两季发挥作用,一来能使屋里凉快些,二来省煤,说到底还是省钱。有些困难的家庭,一年四季都是烧柴火。
即便是“半年柴火半年煤”,我家每年至少也得去北山拉一次煤。每到决定拉煤的重大日子,母亲就会在头天晚上炉几个火烧或烙几张烙馍,用净布裹好,放到一个布包里,以备姐姐拉煤当天当干粮。姐姐则会提前把平车借到家,给轮胎打足气,给车轴抹抹油,再用绳子把后荆挡箍好,作好出发前的一切准备。
村上的人去拉煤,大多会多联络几家,约好时间,一起出发,路上有人做伴,壮个胆,还能有个照应。
今年70岁的姐姐回忆说,当年去拉煤,都是黑咕隆咚就出村了,引得村里的狗不停地叫唤,路过哪个村,哪个村的狗就叫成一片。有时候急行军似的走了三个多小时,到了煤矿,太阳还没有露面。等到人家上了班,先上地磅秤了平车的“皮重”,然后给你开一张条子,就可以去大煤堆前自己装煤了。
装煤是有巧门的,可以“见机行事”。当时,煤面的价格是十三四元一吨,而煤炭的价格要高一些,所以装煤时,趁煤矿管理人员不注意,拉煤的人大多会眼疾手快把一些炭块装在底下,然后再赶紧在上面装些煤面,以期用煤面的价格买回一些煤炭,沾点小便宜。姐姐没有足够的胆量,拉回家的煤里能捡出几块馍头大的煤炭,就算是“大快人心”了。母亲会如获至宝,单独把这几块炭放起来,以备日后生火时让它们发挥重要作用。
往往是装了车,过了磅,付了钱,已经中午了,简单吃几口干粮,在矿上喝几口自来水,姐姐和同去的人不敢歇息,就各自拉起重车,开始紧赶慢赶往回返。
去一趟煤矿不容易,姐姐车上装的煤自然不会比别人少,400多公斤该是有的,走平路相对省气,要是遇到坑坑洼洼不好的路,那就费气了。特别是遇到大上坡时,就更是难上加难了,要么是咬牙瞪眼,提前憋足劲儿利用惯性往上冲,要么是同行的人相互帮忙,先把一辆车推上坡,再回头去推另一辆。
我们村西北方向三四公里外的西常位村北,有一条大沙河,它的河堤高如房脊,势若房坡,重车由北往南过大堤,不要说一个人很难拉车过去,就是一个人用劲儿拉、另一个人可劲儿推,都得齐心协力,使出一身臭汗,费很大的劲儿。如果此时正好有人路过,不管是男是女,或老或少,你只要嘴甜,能喊声大叔大伯或大哥大姐,都会有人不讲代价帮你把车推过大堤。
也就是因为这个大堤的存在,母亲在我姐姐去拉煤的当天下午,往往会心急火燎带上一条绳子,匆匆忙忙步行几公里赶到这里,焦急地等待我姐姐。只要是远远地看到姐姐拉车的身影,母亲就会快步迎过去,把绳子的一头拴到车辕处,另一头搭过肩膀缠在胳膊上,狠命地帮我姐姐拉车,助她一臂之力。
过了沙河大堤,离家就越来越近了,这时候,姐姐才会从系在车把上的布包里掏出干粮,边拉车边吃上几口,为自己补充点能量。
四
一车煤拉到家门口时,要么是后半下午,要么是日薄西山,爷爷、奶奶、哥哥和我,都会一起动手,有的往箩头里装,有的抬,有的挎,热热闹闹把几百公斤煤转移到院里的一角用土盖上,或直接安放到屋里,那种紧张忙碌而又充满欢乐的劳作场面,真的就是最动人的生活画面,最有烟火气,也是一家人最幸福的时刻。
拉回去的煤转移到家后,母亲会圪蹴在刚才卸煤的煤底儿处,左手拿着一个小簸箕,右手握着一把小笤帚,一遍遍清扫煤底儿,那样子恨不得能刮掉一层地皮。直到把地面扫到恢复了本来面目,母亲才会心满意足地端着土多于煤的小簸箕回家。她说,反正煤里还是要搅土的,带点儿土正好。她这样对我们说,表面上是心疼掏钱买来的煤,其实是更心疼我姐姐起早贪黑的辛苦奔波。
有了煤,一家人的生活就有了保障,有了底气,同时也有了温暖。
把胶土搅入煤中再加水,和成半湿不干有黏性的煤泥,就成了日常生活中往煤火窟窿里填充的燃料。这样的日子,在后来有了煤球,又慢慢用上了电磁炉、天然气后,才彻底改变了。
记得1985年我在新乡市一家企业打工,一次回家,母亲说家里的煤快烧完了,我回到厂里后,跟厂领导说了情况,破例免费用厂里的工具车跑到辉县拉了两吨多煤,折腾了100多公里,用时大半天才把煤送到了家门口。当我突然冲进家里,带着终于能为家里解决点实际困难的自豪感,冷不丁地喊母亲和哥哥出来卸煤时,我从母亲慌慌张张又喜出望外的神情里,获得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幸福感,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特别是看到邻居用一种羡慕的目光,看着我们家用汽车一下子往家里拉了这么多媒,像小山头一样,够烧几年的,我心里像喝了蜜一样甜,甚至有点得意扬扬了。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为家里做的有意义的大事,用尽了我两个月的100多元工资,但是很值得。
现在,普通百姓家已很少以煤为燃料来保障一日三餐了,不是用不起,而是有新的更洁净的能源了。但是那几十年烧煤和烧柴的烟火日子,一直是留在几代人心里最有意思、最值得回忆的生活,令人终生难忘,每每想起,都会有一股暖流从周身慢慢通过,犹如冬天围坐在煤火台上,跟家人一起烤火聊天,暖意融融,浑身舒坦。
 豫ICP备14012713号
备案/许可证号:豫ICP备14012713号-1
豫ICP备14012713号
备案/许可证号:豫ICP备14012713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