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详情
2024年12月20日
■“读读写写”之一
书的“机械感染力”
□ 北里汉
这里说的不是内容方面的描写、刻画、情节安排、矛盾冲突等作用于人的情感的感染力,而是形式方面的文字铺排、文字氛围等作用于人的写作的感染力,纯属技术层面的东西,与读者的情感无关,所以我称之为“机械感染力”。
一
最近受到“机械感染”的一个例子是我写的《所谓网友》,这是我在论坛上浸洇了一段时间,有感于网友们的种种可爱之处而写出来的。此文出炉之后,得到了一些网友的青睐,说我写得真实,写出了网友的群体性格,那是我的写作初衷,我承认;有人说我的文笔如何不错,那是鼓励的,我不敢谬领。独有一位网友不是从内容而是从文字上作出了独到的评价:“语速极快。”这个“四字评”,让我心中窃喜。我说:“知道为什么吗?我正在看王蒙的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受到了一些感染。”
爱读王蒙的小说已经29年了。1978年,在《人民文学》上第一次看到他的小说《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小说开头先设问一句:“该怎样为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画像呢?”然后是“是描写……呢?刻画……呢?渲染……呢?同情……呢?羡慕……呢?……”一口气铺排了六七个长句子,对我这样一个热爱写作而往往写了上句想不起来下句,经常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抓住了一个灵感却铺排不开的人来说,只有顶礼膜拜的份儿。这个特点在王蒙后来的小说《春之声》《夜的眼》《说客盈门》《布礼》《蝴蝶》《风息浪止》《坚硬的稀粥》和三年前出版的《青狐》、刚刚出版的两部自传中越来越突出。王蒙往往抓住一个在我看来很不起眼的、很没有挖头的话题,像突然挖出来一个涌水量极大的泉眼,洋洋洒洒地铺排一大段甚至一整页,而且写得如洪水滔滔、汪洋恣肆,读来十分过瘾。而且在这样的铺排当中往往有出其不意的笔法,在纯粹的文学语言中突然来一个“文件体”的词儿如“该同志”之类,在对故事情节的叙述当中突然援引一个人所共知的现实生活中的事件,有时候会在叙事过程中出其不意地加上一大段、一整页似乎离题的东西与小说情节貌合神离,为了对仗他会创造一个“五方逢源”来对应“八面来风”,但是也会在一段整齐的排比当中突然以一句极不协调的句子作结。他的《春之声》,一开头来了这么一句:“‘咣’的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真的是出人意料!怎么这样写啊?什么意思啊?看看下文,才发现是人坐在闷罐车里,铁门“咣”的一声关上,车里就黑了,只有通过方形的车窗投向对面的灯光,描写是绝对真实。
王蒙的这两个特色,第一个我称为“铺排”,第二个我称为“出奇”。我的《所谓网友》,就尽我所能作了大量铺排,虽然朋友以为“语速极快”,可与王蒙的铺排比起来差远了。“嘴边不留半句话,见面即抛一片心,岂止是一见钟情?还没见面就把对方当知己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今万户侯,豪情总是满怀”这两句,也多少有一些出奇之处,但是与王蒙比起来连小巫见大巫也算不上,不过有一点点影子而已。
读某一类文章多了,会影响自己的写作,使自己的行文风格向其靠拢,这是不由自主的事儿。民间说夫妻俩的长相会越来越像,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都是这个理儿。曾经有一个女孩儿拿了几篇自己写的散文让我指教。她写的算是抒情散文,也就是有人说的“小女人散文”,但是语句有些艰涩,我感觉有些疑惑,文章怎么能写成这样?我问她爱看些什么书,她说爱看鲁迅的文章,我“哦”了一声,原来如此啊!鲁迅是干啥的?鲁迅是战士,他的文章处处都有或明或暗的“匕首与投枪”,甚至不乏尖刻,用他的笔法怎么可以抒情?女孩子读错书了,她应该读张爱玲、读铁凝、读宗璞、读王安忆、读乔叶。一般的学习型、爱好型、消遣型读书不用说,假使要学习写作,应该读那些与自己个性接近的作家的与自己想写的题材接近的书或文章,这样更容易收到成效。
二
一位好友在和我谈论写作的时候曾经说过,报纸的文体是一种“报纸体”,言外之意是报纸上的文章要求比较低,不需要多少文采,不需要多少修辞手法,用不着下多大功夫(2005年12月,在北京,就有一位教授在报告席上说:当一个新闻记者,高中学历足矣!)这话虽然语涉调侃,毕竟有一些道理,因为新闻写作在整个大写作的家族里只是一部分,只是一类文体,很多文体的写作技巧在这里用不着,比如诗词的对仗、平仄、用典、意境等。但是新闻写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虽然有自己独特的要求,但也不排斥任何兄弟门类的文体的写作技巧。
况且,所谓“报纸体”是一个大概念,其中也包含不少小概念,各个种类的文体还有着不同的要求。比如消息和通讯,简略一点来说都是记事的(人物通讯也是写人物事迹的),但是写作也有不同的要求。消息要事中见理,没有相当的理性,消息就没有高度和深度,同时也不排斥事中见情的写法。通讯要事中见情,写出感情色彩,赋予感染力,同时也不排斥理,没有相当的理性也就没有高度和深度。言论的要求就更丰富了。社论是站着说话的,要高屋建瓴,有理性、有高度、有自信,甚至要有些“命令式”,在这方面不能“客气”。因为社论是代“司令部”立言的,理应当仁不让。一般的评论是坐在会议桌旁说话的,姿态要低一些,虽然也要有高度、有自信,但不能“命令”。署名评论就更不同了,它是坐在啤酒摊儿上或草地上与朋友对等交流的,要心平气和娓娓道来以理服人,要有足够的谦恭,不然会把朋友吓跑的。
成为新闻人之前我是一个文学写作爱好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拿起《人民日报》就直奔第三版(那时候《人民日报》是4个版,第三版是副刊),写作自然是偏重于文学语言。参加工作后写的第一份单位年终工作总结让单位领导高兴得手舞足蹈(她是文艺兵出身,感情丰沛,喜怒皆形于色),而我搞了二三十年机关工作的大哥看了却说“学生腔”。刚进入报社的时候当一版编辑,对“报纸体”文章很不适应,一落笔总有“学生腔”,我不得不天天看报纸的头版,把中央的重要文件、决定、通知什么的剪贴下来,有时间就看一遍,接受了一段时间的熏陶,也就是“机械感染”才上了道。
某年春节,农历大年初二在老家住了一晚上,次日清早到村外一走,发现蓝天白云煞是好看,顿时起了写一篇抒情散文的冲动。可写来写去总是摆脱不了“报纸体”的腔调,别说写景抒情了,连叙述的语言都写不出来文学的味道。没奈何,读了几天的名家散文,接受了一番“机械感染”,才找到一点感觉。某年3月,报纸要发关于植树节的社论,编辑部的同人约我来写,当时我正在构思一篇散文,满脑子都是文学的词儿,恰巧植树节的社论有发挥余地,就写了一篇散文诗式的社论。这篇社论的开头用几句文学语言描写了大好春光,点明此时正是植树的好时节。然后用三段文字论述植树的意义,当然是用文学的语言,结尾都是“为了什么什么,我们植树去”。最后一段畅想了一番全民义务植树之后遍地绿荫的景况,浪漫了一回。这篇社论见报后得到了一些赞誉,其实没什么,不过是语言活泼一些而已。这样的“四季歌”,再写10年也不会有多少新意,无非是根据当时的中心工作加上发展旅游、建设园林城市等字眼。次年植树节,编辑部的同志又约我写社论,而且还要那样的写法,说是那样的写法很受读者喜爱。我说不行了,一则,这样的创新之举可一而不可再;二则,当时也不在状态,想写散文诗也不容易写出来。
20多年了,形成了这么一个模式:要写社论必须先读文件,找找精神顺便也找找感觉,也就是找找社论应有的语感;要写文学必须先读几天文学,不主动接受一些“机械感染”,就找不到感觉、进入不了状态,喜耶?忧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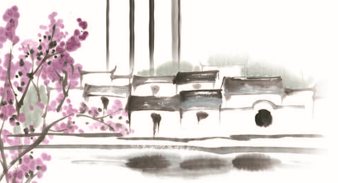
 豫ICP备14012713号
备案/许可证号:豫ICP备14012713号-1
豫ICP备14012713号
备案/许可证号:豫ICP备14012713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