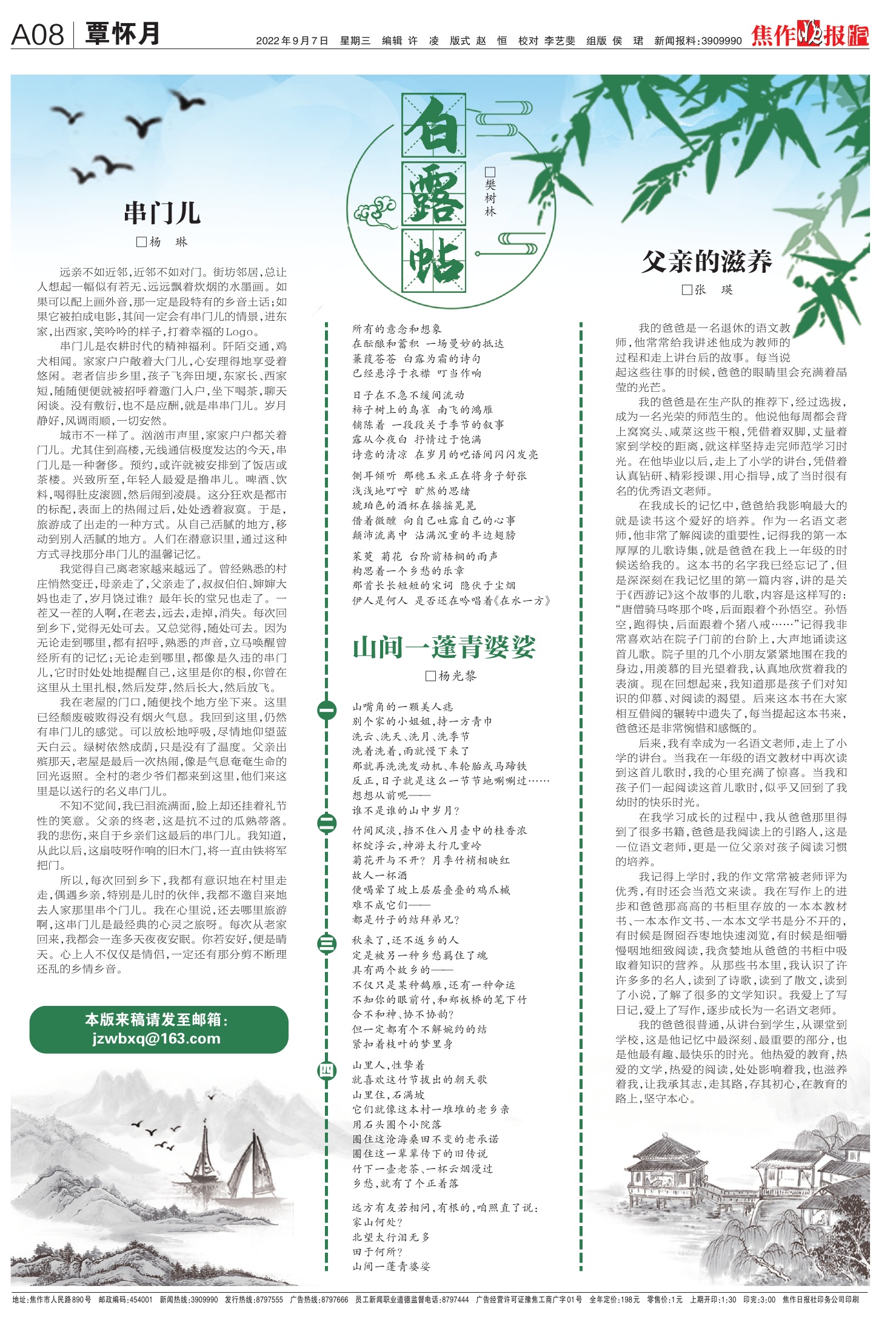еҶ…е®№иҜҰжғ…
2022е№ҙ09жңҲ07ж—Ҙ
дёІй—Ёе„ҝ
в–ЎжқЁ зҗі
иҝңдәІдёҚеҰӮиҝ‘йӮ»пјҢиҝ‘йӮ»дёҚеҰӮеҜ№й—ЁгҖӮиЎ—еқҠйӮ»еұ…пјҢжҖ»и®©дәәжғіиө·дёҖе№…дјјжңүиӢҘж— гҖҒиҝңиҝңйЈҳзқҖзӮҠзғҹзҡ„ж°ҙеўЁз”»гҖӮеҰӮжһңеҸҜд»Ҙй…ҚдёҠз”»еӨ–йҹіпјҢйӮЈдёҖе®ҡжҳҜж®өзү№жңүзҡ„д№ЎйҹіеңҹиҜқпјӣеҰӮжһңе®ғиў«жӢҚжҲҗз”өеҪұпјҢе…¶й—ҙдёҖе®ҡдјҡжңүдёІй—Ёе„ҝзҡ„жғ…жҷҜпјҢиҝӣдёң家пјҢеҮәиҘҝ家пјҢ笑еҗҹеҗҹзҡ„ж ·еӯҗпјҢжү“зқҖе№ёзҰҸзҡ„LogoгҖӮ
дёІй—Ёе„ҝжҳҜеҶңиҖ•ж—¶д»Јзҡ„зІҫзҘһзҰҸеҲ©гҖӮйҳЎйҷҢдәӨйҖҡпјҢйёЎзҠ¬зӣёй—»гҖӮ家家жҲ·жҲ·ж•һзқҖеӨ§й—Ёе„ҝпјҢеҝғе®үзҗҶеҫ—ең°дә«еҸ—зқҖжӮ й—ІгҖӮиҖҒиҖ…дҝЎжӯҘд№ЎйҮҢпјҢеӯ©еӯҗйЈһеҘ”з”°еҹӮпјҢдёң家й•ҝгҖҒиҘҝ家зҹӯпјҢйҡҸйҡҸдҫҝдҫҝе°ұиў«жӢӣе‘јзқҖйӮҖй—Ёе…ҘжҲ·пјҢеқҗдёӢе–қиҢ¶пјҢиҒҠеӨ©й—Іи°ҲгҖӮжІЎжңүж•·иЎҚпјҢд№ҹдёҚжҳҜеә”й…¬пјҢе°ұжҳҜдёІдёІй—Ёе„ҝгҖӮеІҒжңҲйқҷеҘҪпјҢйЈҺи°ғйӣЁйЎәпјҢдёҖеҲҮе®ү然гҖӮ
еҹҺеёӮдёҚдёҖж ·дәҶгҖӮжұ№жұ№еёӮеЈ°йҮҢпјҢ家家жҲ·жҲ·йғҪе…ізқҖй—Ёе„ҝгҖӮе°Өе…¶дҪҸеҲ°й«ҳжҘјпјҢж— зәҝйҖҡдҝЎжһҒеәҰеҸ‘иҫҫзҡ„д»ҠеӨ©пјҢдёІй—Ёе„ҝжҳҜдёҖз§ҚеҘўдҫҲгҖӮйў„зәҰпјҢжҲ–и®ёе°ұиў«е®үжҺ’еҲ°дәҶйҘӯеә—жҲ–иҢ¶жҘјгҖӮе…ҙиҮҙжүҖиҮіпјҢе№ҙиҪ»дәәжңҖзҲұжҳҜж’ёдёІе„ҝгҖӮе•Өй…’гҖҒйҘ®ж–ҷпјҢе–қеҫ—иӮҡзҡ®ж»ҡеңҶпјҢ然еҗҺй—№еҲ°еҮҢжҷЁгҖӮиҝҷеҲҶзӢӮж¬ўжҳҜйғҪеёӮзҡ„ж Үй…ҚпјҢиЎЁйқўдёҠзҡ„зғӯй—№иҝҮеҗҺпјҢеӨ„еӨ„йҖҸзқҖеҜӮеҜһгҖӮдәҺжҳҜпјҢж—…жёёжҲҗдәҶеҮәиө°зҡ„дёҖз§Қж–№ејҸгҖӮд»ҺиҮӘе·ұжҙ»и…»зҡ„ең°ж–№пјҢ移еҠЁеҲ°еҲ«дәәжҙ»и…»зҡ„ең°ж–№гҖӮдәә们еңЁжҪңж„ҸиҜҶйҮҢпјҢйҖҡиҝҮиҝҷз§Қж–№ејҸеҜ»жүҫйӮЈеҲҶдёІй—Ёе„ҝзҡ„жё©йҰЁи®°еҝҶгҖӮ
жҲ‘и§үеҫ—иҮӘе·ұзҰ»иҖҒ家и¶ҠжқҘи¶ҠиҝңдәҶгҖӮжӣҫз»ҸзҶҹжӮүзҡ„жқ‘еә„жӮ„然еҸҳиҝҒпјҢжҜҚдәІиө°дәҶпјҢзҲ¶дәІиө°дәҶпјҢеҸ”еҸ”дјҜдјҜгҖҒ婶婶еӨ§еҰҲд№ҹиө°дәҶпјҢеІҒжңҲйҘ¶иҝҮи°ҒпјҹжңҖе№ҙй•ҝзҡ„е Ӯе…„д№ҹиө°дәҶгҖӮдёҖиҢ¬еҸҲдёҖиҢ¬зҡ„дәәе•ҠпјҢеңЁиҖҒеҺ»пјҢиҝңеҺ»пјҢиө°жҺүпјҢж¶ҲеӨұгҖӮжҜҸж¬ЎеӣһеҲ°д№ЎдёӢпјҢи§үеҫ—ж— еӨ„еҸҜеҺ»гҖӮеҸҲжҖ»и§үеҫ—пјҢйҡҸеӨ„еҸҜеҺ»гҖӮеӣ дёәж— и®әиө°еҲ°е“ӘйҮҢпјҢйғҪжңүжӢӣе‘јпјҢзҶҹжӮүзҡ„еЈ°йҹіпјҢз«Ӣ马е”ӨйҶ’жӣҫз»ҸжүҖжңүзҡ„и®°еҝҶпјӣж— и®әиө°еҲ°е“ӘйҮҢпјҢйғҪеғҸжҳҜд№…иҝқзҡ„дёІй—Ёе„ҝпјҢе®ғж—¶ж—¶еӨ„еӨ„ең°жҸҗйҶ’иҮӘе·ұпјҢиҝҷйҮҢжҳҜдҪ зҡ„ж №пјҢдҪ жӣҫеңЁиҝҷйҮҢд»ҺеңҹйҮҢжүҺж №пјҢ然еҗҺеҸ‘иҠҪпјҢ然еҗҺй•ҝеӨ§пјҢ然еҗҺж”ҫйЈһгҖӮ
жҲ‘еңЁиҖҒеұӢзҡ„й—ЁеҸЈпјҢйҡҸдҫҝжүҫдёӘең°ж–№еқҗдёӢжқҘгҖӮиҝҷйҮҢе·Із»Ҹйў“еәҹз ҙиҙҘеҫ—жІЎжңүзғҹзҒ«ж°”жҒҜгҖӮжҲ‘еӣһеҲ°иҝҷйҮҢпјҢд»Қ然жңүдёІй—Ёе„ҝзҡ„ж„ҹи§үгҖӮеҸҜд»Ҙж”ҫжқҫең°е‘јеҗёпјҢе°Ҫжғ…ең°д»°жңӣи“қеӨ©зҷҪдә‘гҖӮз»ҝж ‘дҫқ然жҲҗиҚ«пјҢеҸӘжҳҜжІЎжңүдәҶжё©еәҰгҖӮзҲ¶дәІеҮәж®ЎйӮЈеӨ©пјҢиҖҒеұӢжҳҜжңҖеҗҺдёҖж¬Ўзғӯй—№пјҢеғҸжҳҜж°”жҒҜеҘ„еҘ„з”ҹе‘Ҫзҡ„еӣһе…үиҝ”з…§гҖӮе…Ёжқ‘зҡ„иҖҒе°‘зҲ·д»¬йғҪжқҘеҲ°иҝҷйҮҢпјҢ他们жқҘиҝҷйҮҢжҳҜд»ҘйҖҒиЎҢзҡ„еҗҚд№үдёІй—Ёе„ҝгҖӮ
дёҚзҹҘдёҚи§үй—ҙпјҢжҲ‘е·ІжіӘжөҒж»ЎйқўпјҢи„ёдёҠеҚҙиҝҳжҢӮзқҖзӨјиҠӮжҖ§зҡ„笑ж„ҸгҖӮзҲ¶дәІзҡ„з»ҲиҖҒпјҢиҝҷжҳҜжҠ—дёҚиҝҮзҡ„з“ңзҶҹи’ӮиҗҪгҖӮжҲ‘зҡ„жӮІдјӨпјҢжқҘиҮӘдәҺд№ЎдәІд»¬иҝҷжңҖеҗҺзҡ„дёІй—Ёе„ҝгҖӮжҲ‘зҹҘйҒ“пјҢд»ҺжӯӨд»ҘеҗҺпјҢиҝҷжүҮеҗұе‘ҖдҪңе“Қзҡ„ж—§жңЁй—ЁпјҢе°ҶдёҖзӣҙз”ұй“Ғе°ҶеҶӣжҠҠй—ЁгҖӮ
жүҖд»ҘпјҢжҜҸж¬ЎеӣһеҲ°д№ЎдёӢпјҢжҲ‘йғҪжңүж„ҸиҜҶең°еңЁжқ‘йҮҢиө°иө°пјҢеҒ¶йҒҮд№ЎдәІпјҢзү№еҲ«жҳҜе„ҝж—¶зҡ„дјҷдјҙпјҢжҲ‘йғҪдёҚйӮҖиҮӘжқҘең°еҺ»дәә家йӮЈйҮҢдёІдёӘй—Ёе„ҝгҖӮжҲ‘еңЁеҝғйҮҢиҜҙпјҢиҝҳеҺ»е“ӘйҮҢж—…жёёе•ҠпјҢиҝҷдёІй—Ёе„ҝжҳҜжңҖз»Ҹе…ёзҡ„еҝғзҒөд№Ӣж—…е‘ҖгҖӮжҜҸж¬Ўд»ҺиҖҒ家еӣһжқҘпјҢжҲ‘йғҪдјҡдёҖиҝһеӨҡеӨ©еӨңеӨңе®үзң гҖӮдҪ иӢҘе®үеҘҪпјҢдҫҝжҳҜжҷҙеӨ©гҖӮеҝғдёҠдәәдёҚд»…д»…жҳҜжғ…дҫЈпјҢдёҖе®ҡиҝҳжңүйӮЈеҲҶеүӘдёҚж–ӯзҗҶиҝҳд№ұзҡ„д№Ўжғ…д№ЎйҹігҖӮ
жң¬зүҲжқҘзЁҝиҜ·еҸ‘иҮійӮ®з®ұпјҡ
jzwbxq@163.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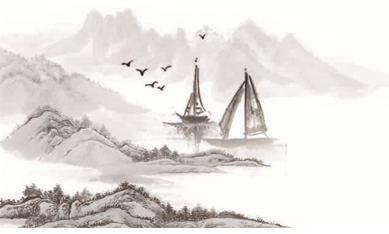
 иұ«ICPеӨҮ14012713еҸ·
еӨҮжЎҲ/и®ёеҸҜиҜҒеҸ·пјҡиұ«ICPеӨҮ14012713еҸ·-1
иұ«ICPеӨҮ14012713еҸ·
еӨҮжЎҲ/и®ёеҸҜиҜҒеҸ·пјҡиұ«ICPеӨҮ14012713еҸ·-1